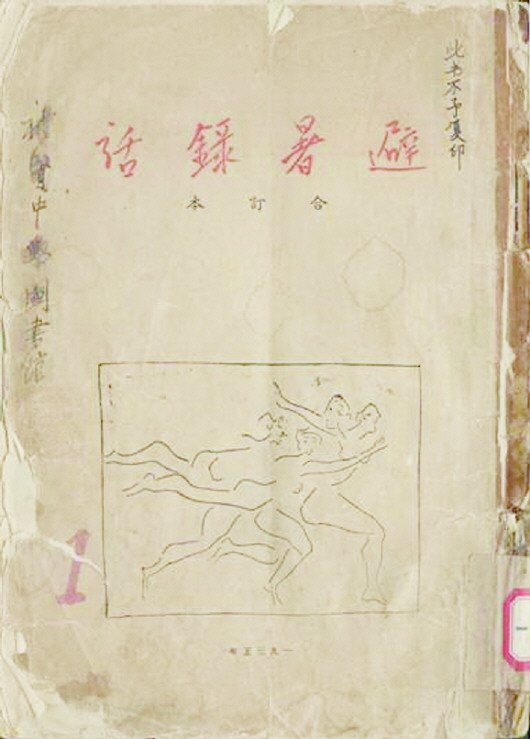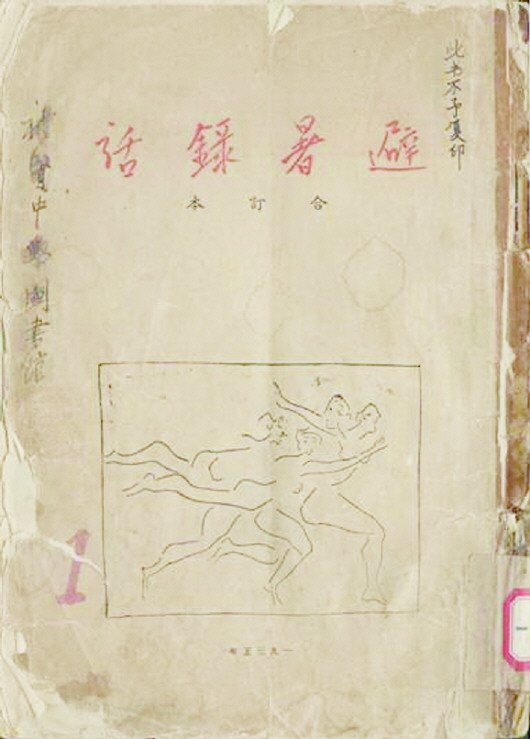
《避暑录话》合订本封面,青岛礼贤中学收藏本。

上世纪30年代青岛第一海水浴场
□柳已青
1935年的盛夏,《避暑录话》在青岛落地生根,王统照、洪深、老舍、吴伯箫、孟超、赵少侯、臧克家、王余杞、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刘西蒙,12位作家的文学作品精彩纷呈,一股来自历史深处的凉风,为岛城带来阵阵清爽!
《避暑录话》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上世纪30年代,虽然日寇步步紧逼,中原板荡,国事蜩螗。但在国内出现了一个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对于青岛来说,不论文化还是教育事业,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地利,一方面是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创立,吸引了国内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在此弦歌不绝,为国化育人才;另一方面,青岛是国内重要的港口城市,国际闻名的避暑和旅游胜地。人和,国立山大在青岛经过五六年的发展,开始发挥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影响力,人文学科和海洋科学两翼齐飞,大师云集。同时,青岛也吸引众多名流客居青岛,留下诸多文化的资源。
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契机。在一次作家聚餐会上,桌上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作家和诗人的聚餐,皆是诗酒风流客,喝得酣畅淋漓之时,有人提议,在《青岛民报》开设一个文艺副刊,为青岛文艺的发展,做点事情。结果,一呼百应。如同王亚平《老舍与避暑录话》所说:既然大家相聚在此,就应该“干点事儿,不能荒废下去。”于是决定,给《青岛民报》办一个副刊,借避暑之名谈点心里话,故取名为《避暑录话》。1935年7月14日,依托《青岛民报》而实则独立编排、装订、发售的文艺副刊《避暑录话》诞生了。
一个文艺副刊的名字为何叫“避暑录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诞生在避暑胜地青岛的地理属性,一是来自古代笔记中的典故。老舍对刊名解释是:“宋朝,有个刘梦得,博古通今,藏书三万卷,论著很多,颇见根底,这个《避暑录话》,也是他的著述,凡二卷,记了一些有考证价值的事。我们取这个刊名,要利用暑假,写些短小的诗文。”戏剧家洪深写了发刊词,作题解:“避暑者,避国民党老爷之炎威也。”“否则他们有沸腾着的血,焦煎着的心,说出的‘话’必然太热,将要使得别人和自己,都感到不快,而不可以不‘录’了!”归根到底,《避暑录话》的诞生,其宗旨是文章合时而著,文艺为时代和大众鼓与呼!刊头的“避暑录话”四字,也是出自洪深之手。
“《避暑录话》副刊虽小,阵容不弱。老舍的散文,亲切中洋溢着幽默,让你像听着最熟悉的朋友作漫不经心的絮语,和他一起吟味着生活的温馨与苦涩。洪深是左右开弓,一面关注戏剧,也创作,也研究。孟超、亚平、同愈写诗,吴伯箫写散文。王统照的诗文有的描写北国特有的农作物蜀黍(高粱),有的描述山东夏晚的黄昏景色,后来大都收入《夜行集》、《青纱帐》中。”青岛大学教授刘增人如此描述。
《避暑录话》刊发的文章,可谓有趣,有料,可读,可亲。文章类型丰富多彩,散文、随笔、新诗、短篇小说、文艺评论、古体诗词……老舍的散文风趣幽默,有浓郁的生活滋味和青岛风情,他在《避暑录话》发表的《暑避》一文,尤其脍炙人口,直到今天,生活在青岛的人们,每到夏天,接待外地亲友游览青岛,读到此文,感同身受,也会会心一笑。王余杞在《避暑录话》上写了一篇章回体形式的文章,题为《一个陌生人在青岛》,从第一期开始,到第九期结束,成了连载。值得一提的是,洪深收到田汉邮寄自监狱的诗词,加以注释,发表出来。1935年初,田汉因创作了进步话剧《回春之曲》,触怒国民党当局,被捕入狱,在狱中以诗词明志,抒发胸臆。“江山已待争兴废,朋辈都堪死共生。壁上题诗君莫笑,明朝又是石头城。”洪深冒着风险将田汉的诗词发表,可见两人是莫逆之交,生死之交。
《避暑录话》1935年9月15日终刊,历时两月,每周一期,零售大洋3分,共出10期,发表66篇诗文。这份文艺周刊,远销太原、北平。回望81年前的这份报纸文艺周刊,深感其犹如一座海滨的灯塔,放射出温暖而指引性的光芒。在风雨如晦的时代,作家们鸡鸣不已,记录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避暑录话》带有很强的时令色彩,因暑热而生,临秋风而凋。正如曾广灿在《老舍与“避暑录话”》一文所说:一份典型的同仁出版物,它充满文化人特有的灵感质素,却没有半点书卷气,处处显示着这群文化人“诗心苦、文骨遒”的高贵品格。
心驰神往那片海
□曲海波
1935年出版的《青岛风光》曾记述:“海水浴场至为完备者,厥为汇泉海岸……沿岸有板房更衣室林立,以供浴客更换衣服或浴罢休憩之用……至于浴用器械,有跳台、浮台、舢板、救生圈等物,设备至为完全,初辟太平路栈桥西岸浴场……临时备有汽艇多艘,雇用熟习水性者,从事预防救护,插定浮标,庶于限制之中,仍寓保护之意,继又辟湛山海水浴场、太平角海水浴场、山海关路海水浴场,均属地势优越,风景天然……而各场秩序井然,实为其他省市所未有。”由此可见,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为吸引游客洗浴消夏,对海水浴场的管理已很成熟规范。
在国立山东大学执教的梁实秋先生,在《忆青岛》一文中,最令其心动的便是和家人在青岛海滩上的欢愉时光:“青岛之美不在山而在水。汇泉的海滩宽广而水浅坡度缓,作为浴场据说是东亚第一。每当夏季,游客蜂拥而至,一个个一双双的玉体横陈,在阳光下干晒,晒得两面焦,扑通一声下水,冲凉了再晒。其中有佳丽,也有老丑。玩得最尽兴的莫过于夫妻俩携带着小儿女阖第光临。小孩子携带着小铲子小耙子小水桶,在沙滩上玩沙土,好像没个够。更妙的是下面岩石缝里有潮水冲积的小水坑,其中小动物很多。如寄生蟹,英文叫‘hermit crab’,顶着螺蛳壳乱跑,煞是好玩。又如小型水母,像一把伞似的一张一阖,全身透明。”
1934年的夏天,杭州酷热难挡,“路上柏油熔化,中暑而死者,日有七八人”。7月13日至8月12日,应旅青友人汪静之、卢叔桓之邀,作家郁达夫携妻子来青岛避暑,整整住了一个月。在轮船行驶的大海上一看到青岛,他就爱上了这座城市:“……白的灯台,红的屋瓦,弯曲的海岸,点点的近岛遥山,就净现上你的视界里来了,这就是青岛。所以海道去青岛的人对她所得的最初印象,比无论哪一个港市,都要清新些,美丽些。”后来郁达夫没能再履青岛,但青岛的风景,一直使他无法忘怀。1934年底,他坐在杭州的寓所里写游记,还念念不忘“在东亚,没有一处避暑区赶得上青岛的”。
臧克家1930年破格考取国立青岛大学后,在青岛学习生活的五年中,坐听涛声起落,卧看云走霞飞,经历了大革命血与火考验的他度过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段从容。1956年重来青岛,他兴奋地写了《青岛解放我重来》:“我们住的地方十分幽静,坐在小楼上,就可以看到大海,深夜醒来,就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晌午,躺在床上,想闭闭眼,朦胧中听到大海的呼唤,它的魅力像一条拉你的彩缰,于是,拿起浴衣,呼几个同伴,几分钟后,身子便游动在大海之中了。沙滩上有大人,有孩子,有男的,有女的。彼此是陌生的,但交换着亲切的目光,比赛着各自捡到的晶亮的贝壳,不论大人孩子,全是赤身赤心,全成为大自然的儿童。”
1935年夏天,时在武汉大学教书的苏雪林“为了享受新秋似的清凉”,携同丈夫来到青岛避暑,下榻位于福山路的山东大学教职员宿舍。苏雪林虽然在青岛只小住了一个月,却为青岛留下了《岛居漫兴》和《崂山二日游》两篇大文章,计5万余字,并在1938年出版了《青岛集》,几乎把青岛所有的风景胜地都收拢笔下。在《岛居漫兴》之《汇泉海水浴场》一文中,其对青岛海水浴场的赞美之情,跃然纸上:“青岛共有五个海水浴场,汇泉地点最适中,形势最优胜,一到夏季,红男绿女,趋之若鹜,使这地方成为最热闹的顶点,欢乐的中心,消暑的福土,恋爱的圣地……两个环抱的海岬中间是一片宽约数里的大海湾,可以容纳数万个弄潮儿同时下水。快乐的情调,泛滥在海面上,在林峦间,在变幻的光影里,在无边无际的空间。”
夏季的青岛,本就是避暑胜地,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更是众多文人学者吹吹海风、洗洗海澡的消夏舒心之地,甚至在81年前的盛夏,王统照、洪深、老舍等12位作家、学者相聚青岛,大家文兴袭来,不想当“专为避暑而来的真正闲者”,于是在《青岛民报》开设了文艺副刊——《避暑录话》。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