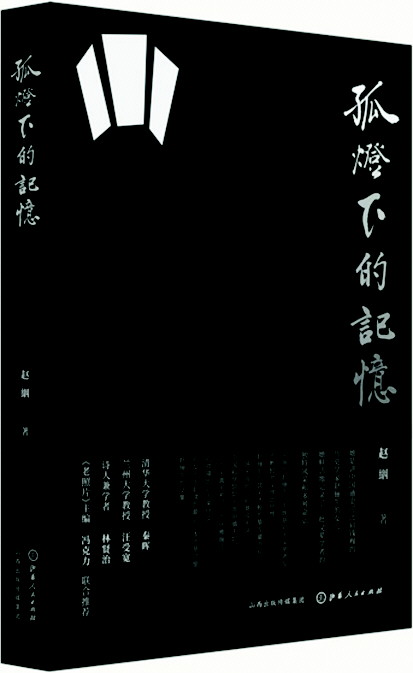赵絪与父亲赵俪生,1947年摄于河南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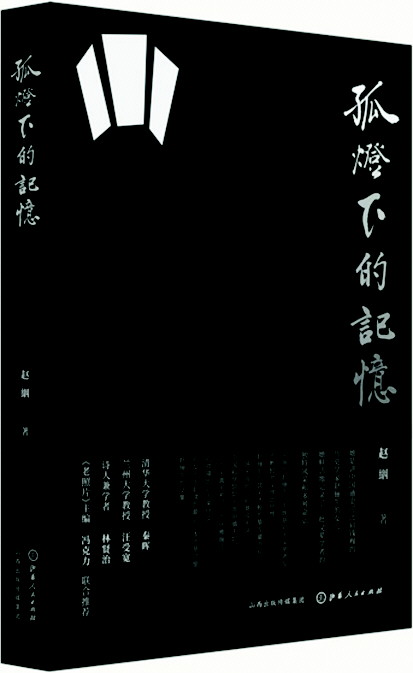
《孤灯下的记忆》
赵絪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大岁月:边做学问边培养爱好
在赵俪生高昭一夫妇的六个子女中,赵絪是第三个女儿,1946年初生于陕西蔡家坡。赵家夫妇带着孩子在几所大学间颠沛流离:从河南到华北,由华北而济南,再从济南进北京,又从北京到长春——几年间,竟辗转了不少学校。直到1950年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后,才度过了比较安稳的七年时间。解放初期的山东大学,名流云集、人才济济,赵絪姊妹们和生物学家童第周、古生物学家周明镇等名教授的孩子们都是好友。赵家住在蓬莱路一号的一幢德日风格别墅庭院,让王瑶、顾颉刚等从北京来的好友羡慕不已,一入夏便纷纷来此地避暑。
上世纪50年代的文人收入颇丰,山东大学的教授圈子也流行着各种兴趣爱好,赵俪生唯喜喝浓茶、听京剧、收藏字画。
赵俪生喝茶的浓度,用画家陈伯希的说法,“可以药死一只耗子”,还动不动就“淡了,再沏一壶”。在山大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小孩跟在赵俪生身后拍着巴掌,学着他的腔调:“青岛,青岛,谁家的茶叶最好……”
当时四大名旦轮流来青岛演出,赵俪生在看戏方面不惜花钱,有时请同事朋友们一起看,过后再认真地讨论评价,从编剧、唱腔到表演,各抒己见。青岛话剧团、京剧团演出新编剧时,他常被邀请担当历史顾问。每个名角到青岛,报纸都会留出版面,等赵俪生过完戏瘾,连夜提笔著文。
1957年前赵俪生的月收入在八百元以上,在当时养活几十口人也不成问题,却从未存下钱,差不多都被赵俪生送到古董字画店了。有一次赵俪生收到了一笔两千元的稿费,这在当年称得上一笔巨款,妻子高昭一也学着其他教授太太在银行里存了定期。赵俪生却非要拿到这笔钱不可,三天三夜闹个不停。高昭一拗不过,只好取出钱交给他。赵俪生转身出了门,没两个时辰,坐着洋车回来了,脚下两三个瓶瓶罐罐,腋下夹着几轴字画。
通过对这些爱好的深入研究,赵俪生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文艺、美术评论文章。而且受他的影响,子女们对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个个能写会画。
读书教书:在苦难中磨砺人生
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赵俪生被下放到河西走廊山丹县四十里铺的师大农场去劳动。在戈壁荒滩严酷的生存条件下,他竟侥幸生还。家里人最了解赵俪生,除了家中捎寄到农场的一点点吃的,让他活下来的还有精神食粮——读书。无论是夜卧地铺或是放马途中,他枕边和手中拎的总是一本《国语》或《左传》,以此疗饥。
“文革”中期,赵俪生只要闲在家中,还是忘不了读书,偷偷地著文,漫步于学林书海中。这期间完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史》的写作,对《聊斋志异》的重要篇章进行了剖析,并写了大量论文。他估计此生所有已完成的著作难见天日,故在书稿后面写上“篱槿堂遗稿”的字样。
后来赵俪生再度被下放至永登干校,下工后,依然是小油灯下自读自乐。
赵俪生这一生在任何境况下不忘读书,只要有书读,怎样都可以。在女儿赵絪看来,天赋、勤奋造就了父亲一个史学家最基本的条件,而二十多年在劫难逃的苦难,“铸就了他更加深沉、更加稳健的一代学人必备的素质”。
这对于子女们是个榜样。“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忘读书,各式各样的书都读。那时候能读到的书很少,但有幸父亲的藏书比较多。我们虽然穿得很朴素,但我们没有自卑过。那正是读书无用论的时候,但父亲告诉我们要阅读、要记录、要写文章。有时候讲年谱,他会把历史上很枯燥的问题讲得非常生动,像讲故事一样,无形中对我们是一种感染。”赵絪如是说。
尽管赵俪生的教学生涯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而时断时续,依然给听课的学生留下了恢宏大气、不死板、不教条的印象。1961年,他承担了兰州大学新进校学员的基础课——中国通史,赢得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讲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下半叶讲得最好的,当数兰州大学的赵俪生”的盛誉。
1978年,赵俪生一下子招收了七名研究生,他以爱犊之心将这七名学生喻为“七只九斤黄”,基础课和专业课全由他一人包揽。名义上是七名学生,教室里却挤得满满的,文科高年级本科学生和研究生都来听他的课。上完课回到家,即便隆冬季节,他的衬衣衬裤也都被汗水浸透了,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来。
同侪友人:一代学人的掌故
赵絪在书中还记录了其他知识分子如王瑶、周明镇、童书业等的独特风采和多舛命运。
王瑶曾揶揄过赵俪生的婚姻,“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赵絪姐妹自然耿耿于怀。1953年,王瑶到山东大学看望赵俪生时,刚上小学的赵絪和两个姐姐席地而坐,排成一排,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王瑶指着啦啦队责问:“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赵俪生一边“去去去”地轰女儿,一边不以为然地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在赵絪看来,王瑶与父亲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两人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击,却又彼此牵挂、欣赏,嘴上却从来不买账不服输。就是到老,暗中较劲也没减势。王瑶寄来《王瑶文集》七大本,赵俪生放置案头,发誓“将来我的文集出来,绝不比王瑶兄差”。《赵俪生文集》刊印出来后,赵俪生击案长叹:“可惜王瑶老哥看不到了!”
童书业是赵俪生在山东大学任教时交往最频繁、感情最诚挚的同行好友。童书业最爱到赵家“谈学问”,赵俪生夫妇对他很欣赏,他也是赵家全家老少欢迎的客人。赵絪姊妹一听说童先生到,立马聚到书房去听他发高论、讲典故、谈趣闻,连保姆都抽空倚在门旁边剥葱边听着。花甲之年的赵絪回忆童书业和父亲的友谊,才明白当年的“童伯伯”是何其苦闷,“他非常需要有一个接纳他的场地来宣泄他的情绪,抒发他的心得与体会。”
山东大学古生物学家周明镇与赵俪生的兴趣爱好和学术研究都未有交集,却通过孩子们的友谊开始了两家大人的来往。赵俪生一家着装极为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破破烂烂”;周明镇留美归来,妻子一直在台湾从事文艺教育工作,所以相当“港派”。赵家的“土”和周家的“洋”在山大形成了极大反差。尽管如此,周明镇很赞赏赵俪生的家教与学问,甚至曾有意撮合二儿子与赵家三女儿的婚事。
子女教育:开放自由,不设禁区
赵俪生对于子女的文化教育是自由开放式的,从未设过“禁区”。
读什么书,全凭孩子们由着性子自由翻读,童年时代就把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甚至《金瓶梅》囫囵吞枣地读完了。少年时代的赵絪辍学在家,母亲不许她出门,父亲却向母亲求情:“让她疯去吧,能疯出个好身体来也行。”看戏归来,姐妹几个披上床单为父母模仿一段《断桥》,虽幼稚低劣,父亲却总是予以鼓励和称赞,从不打消孩子们萌发出的任何奇想。遇到生僻字,赵絪懒于查字典,总是去问父亲,父亲就抓住机会给她上一堂说文解字课。
与许多学人家庭与众不同的是,别人家父母间的事,子女知之甚少,于是平时很安静的家庭一来运动,就容易发生“划清界限”的行为。在赵家,父母一吵,子女们迅速分成爹派、娘派开始辩论,跟父亲意见相左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出言不逊。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子女们从小就无视权威,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性格,树立了较为独立自由的思想。赵家子女对父母了解透彻,于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平时喜欢争辩的一家人,凝聚力却要坚固得多。在特殊的岁月里,达官贵人、文化名人家中频传自杀消息时,饱受二十多年煎熬的赵家中却无一人绝望。赵俪生不断用历史的眼光告诫子女:熬下去,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作为父亲,赵俪生总能发现孩子身上的潜质,想方设法把它调动起来,潜移默化地引上正途。赵絪自认为是父母最不成器的孩子,其余姊妹都完成了高等教育,从事学术工作,唯有热爱绘画、一心想报考美院的她却由于不可抗的时代因素,仅有初中学历,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白丁”。即便这样,赵俪生夫妇从来没有放弃对这个女儿的培养与教导。在从农场回来至1966年之间那段稍微平缓的岁月里,赵俪生鼓励辍学在家的赵絪去兰大中文系“蹭课”;因为赵絪有绘画的天赋,赵俪生想尽一切办法让名家指点女儿。直到他到了耄耋之年,赵絪也退休了,他还一直鼓励、指导女儿写作,夸她的文章“立住了”。
在赵絪眼中,父亲只是一介布衣,但给后代留下了一生受用的宝贵财富,那就是不忘读书、勤于笔耕,这本书便是她回报父母教养之恩的一份迟交的“作业”。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