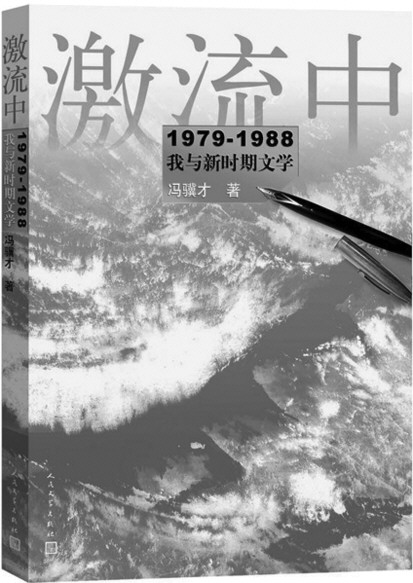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冯骥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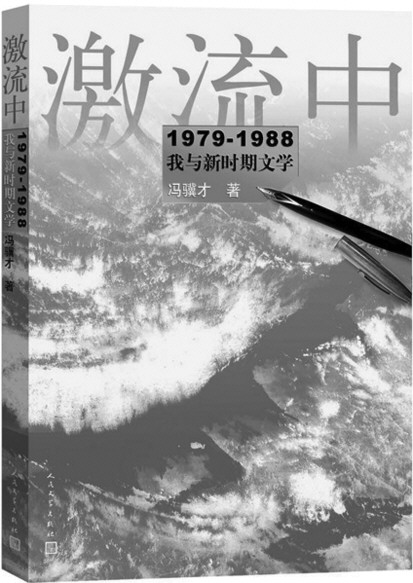
《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写作《凌汛》和《无路可逃》时,冯骥才就有一个明确的写作计划:用一种讲述自我人生经历的方式,以十年为一部书,写一套展示他五十年(1966—2015)生命历程的心灵史,“这种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命运,不是指遭遇,而是精神的历程”。如今,这部心灵史的讲述推进到了激流奔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冯骥才最近出版的《激流中》一书展现了那个年代文坛内外的人情、世情以及对新时期文学现象的反思。
近二十年来,冯骥才致力于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去年10月,在意大利寻访古城古迹时,他强烈地感受到西方人在文艺复兴时期所爆发出的激情与创造力,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创作灵感喷薄而出,便有了这本《激流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冯骥才凭借《三寸金莲》《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等作品驰骋文坛。在一部作品的写作高潮中,冯骥才脑子里会突然冒出一个更强烈的故事和人物,半夜突然起床披衣伏案挥笔是常有的事。他的每一部作品发表后,都会引来成百上千封读者来信。为了更多地了解读者的反馈意见,冯骥才不得不自制了一个大信箱,开信箱时还得用个敞口的提篮接着,不然箱子一打开,里面的信会“喷涌而出”,散落一地。看到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读者的感受和肺腑之言,冯骥才深深意识到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职责——“作家应是人民的代言人”,自觉地把自己钉在“时代责任”的十字架上。冯骥才坦言自己同“文革”刚刚过去的那一代作家都是“责任的一代”,近二十年来他从文学创作转身去做民间文化遗产拯救与保护,仍然出于一种责任。
在新书里,冯骥才讲述了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经历、生活经历,也记录了他与巴金、冰心、王蒙、陆文夫、张贤亮、李陀等著名文学家的交往历程,展示了生动而珍贵的八十年代文坛细节。“文革”后冯骥才的小说《铺花的歧路》曾得到巴金的提携,当他的小说《啊!》引发争议时巴金公开表示支持,至今他仍能感到巴金对他的有力支撑。冰心曾对冯骥才说:“你的工资是人民给的,你必须替人民说话,不要怕!”文学前辈的影响不止于文学,更是一种知识分子精神的传承。
在冯骥才眼里,那个年代“文学就是文坛,文坛就是文学”。1980年冯骥才生病时感受到了来自文坛的关切,很多作家朋友写信问候病情,陈建功听到他去世的误传后据说还哭了一场。文坛上每一篇新鲜独特的作品出现,都会引来作家们的热切关注,并争相传阅,到处打听作者是何方人氏。对作品有歧见者必定会著文争议,相互批评也是常事。1982年为了冲破文学形式的禁区,冯骥才同李陀、刘心武以书信的形式讨论“现代主义”的文章一起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引起了文坛重视。从此,“一道挡住文学前进的铜墙铁壁就这样推开了”。冯骥才也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小说”——一种西方现代派之外的、深植于家乡天津的现代小说,这就是他的《怪世奇谈》系列——《神鞭》《三寸金莲》和《阴阳八卦》。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冯骥才的写作走向自我,“我不关心文坛了,文坛也不像八十年代中期那么纯粹了”。1988年,他去中国美术馆参加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式,看了一圈“荒诞不经”的展览后,对妻子说“我觉得一切都在变了”,同时“好像也找不到读者了”。两年后,在一篇名为《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文章里,他的想法表达得更加明确:“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我们心中愈来愈淡薄。那个曾经惊涛骇浪的文学大潮,那景象、劲势、气概、精髓,都已经无影无踪,魂儿都没了,连这种感觉也找不到了。何必硬说后新时期,应当明白地说,这一时代结束了,化为一种凝固的、定形的、该盖棺论定的历史形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