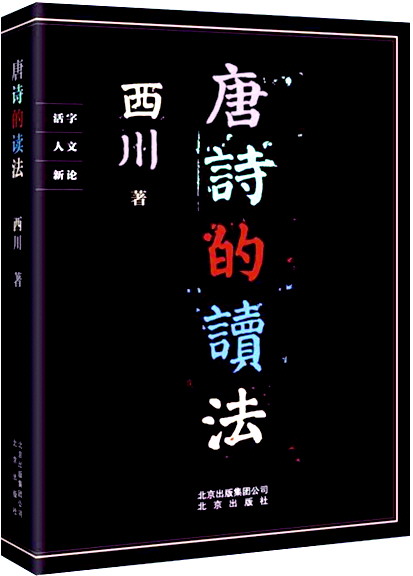刘松年《十八学士图》(局部),描绘唐十八学士游艺于琴棋书画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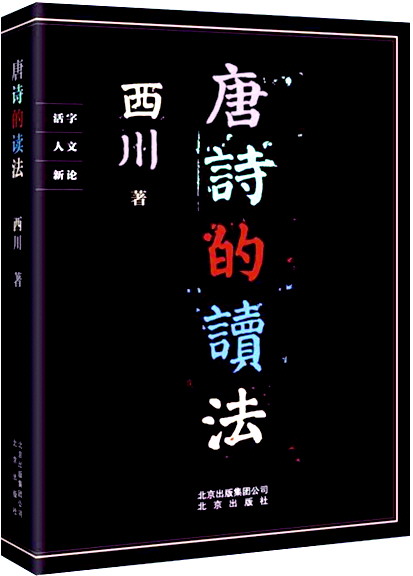
《唐诗的读法》
西川 著
北京出版社
唐诗三百首 不过是冰山一角
西川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去美国做过访问学者,曾翻译过庞德、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最早模仿着《水浒传》里“有诗为证”写旧体诗,上大学后开始写新诗。他坦言研究外国文学只是一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和思考从未停止过。与从古诗词中获得修养相比,他更在意的是探索古人创作的秘密。
现代人提起唐诗,马上就会想到《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是清朝蘅塘退士基于对传统蒙学读本《千家诗》的不满,而为发蒙儿童重新编选的唐诗读本,共选唐代七十七位诗人的作品,约三百余首诗。“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蘅塘退士在序言中的这句俗语表明了此选本的意义:它既是对唐诗进行审美欣赏的选本,同时也是后代诗人进行诗歌写作的范本。
按照西川的说法,拿《唐诗三百首》作为讨论唐诗的读本,如同今天我们以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文章作为讨论文学的标准,“谬之至也”。“三百首”不过是冰山一角,领悟到的是唐诗“没有阴影的伟大”,却看不到唐代的社会状况、文化状况、思想状况。读“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的《全唐诗》,扩大唐诗阅读范围,努力成为唐代诗人的同代人,置身他们的时代背景,才有可能找到读懂唐诗的秘密通道。西川发现《全唐诗》中大部分是应酬之作,也有平庸之作。例如,号称“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见于《全唐诗》的作品还有一首名为《代答闺梦还》,写得稀松平常,简直像另一个人的作品。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元朝人萧士赟认为它写得松松垮垮,甚至怀疑这是伪作。作为写作者,“只有知道古人写得不好的,才知道什么是好”。
在常人眼里,古代诗人都是书生,古诗都是五七言律绝,都押韵用典,但在研究过《全唐诗》的西川看来,他们每个人的禀赋、经历、信仰、偏好都不一样,他们之间有辩驳、争吵、对立、互相瞧不上,也有和解、倾慕。李白与杜甫相知相惜,两个人可以“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韩愈曾邀白居易同游曲江,却被白居易婉拒了,两人关系显得很微妙;同年龄的李白和王维从来不同框,好像互相瞧不上对方,他们的诗集中找不到二人交集的痕迹;诗人之间也相互靠拢、唱和,元稹为杜甫撰写墓志铭、为白居易诗集作序,杜牧称赞韩愈、为李贺诗集作序,李商隐称赞杜牧、为李贺作小传。了解了古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进入他们的时代。如西川所说:“一旦了解了一个时代诗人之间的看不惯、较劲、矛盾、过节、冷眼、蔑视、争吵,这个时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铁板一块,就不再是诗选目录里人名的安静排列,这个时代就活转过来了。”
读懂唐诗,要先读懂那个时代
时常有人站在古诗的立场上批评新诗,西川在参加诗歌活动时也经常遇到有人拿中国古典诗歌来批评中国当代诗歌。西川的观点是,古诗是在古汉语基础上产生的,新诗是现代汉语的产物,两者功能也不同,现代人以为读点唐诗就能写古体诗,其实写的只是现代汉语思维下的诗化的词。丰富的古典诗歌在今天看来是文化遗产,但它们在被写出来的时刻并不是遗产,和写作者的当代生活、历史事件、时代风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背后还有科举制度、古代思想、儒家道统,因此不能简单地拿来给当代诗歌做参照。
正是因为科举制度以及进士文化的存在,如果不熟悉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记》、《汉书》等,唐诗中“古诗用典”客观上就已经将普通读者排除在外了。李白写了通俗如大白话的“床前明月光”,但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把他“随意拉到身边来”,在“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中,李白就采用了孔子以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作为《春秋》结束的典故。但求“老妪能解”的白居易也并不真正在乎把老太太培养成他的“铁杆粉丝团”,即使悯农,他也是说给元稹、刘禹锡听的,他诗歌中的私人叙事性、士大夫趣味、颓靡中的快意、虚无中的豁达,根本不是当代人浅薄的励志正能量语录。古人写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与公众对话,而是与有同等学识、相似趣味的士子进士们之间进行私人交流。
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发音来阅读以中古音写就的唐诗,这本身就有问题,很多人还自以为是地分析出唐诗的立意之高、用语之妙。人们普遍推崇李商隐为晚唐最重要的诗人,认为其作品隐晦、复杂、多用典、常伤悼、靡丽、雕丽、忧郁、眷恋、“夕阳无限好”,这些品质代表了晚唐诗的一部分特色与内容。蒋勋在《蒋勋说唐诗》中说李商隐表达的是“盛世将要结束的最后挽歌”,但西川发现李商隐喜欢夕阳、夕曛、斜阳、残阳、黄昏、薄暮、暮景、暮霞、暮鸦、晚、山晚,反复多次写到这个时间段和这个时间段的景物,很难说这是他的历史感使然。尽管李商隐看到了那个时代宫廷、社会的种种问题,但西川并不认为他具有先知先觉的能力,“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能更多是从李商隐个人的“窝囊”感受出发写下的诗句。“拔高他的历史预测能力其实没有必要,他的性格只是吻合了历史的走向”。
当代诗歌写作不必回到唐朝
写诗是唐朝文化人的生活方式,赴宴要写诗,送别要写诗,游览要写诗,高升或贬官要写诗,人生大事要写诗,无所事事要写诗,他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灵感?其实诗人也有灵感枯竭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写作参考书”便派上用场,如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黄滔的《泉山秀句》、王起的《文场秀句》等,这类参考书的风行,使得唐朝诗歌从题材到趣味都成为一种类型化写作。唐人写诗也非全部脱口而出,一挥而就,李商隐写作诗文时,为了使用典故,常常要查阅许多书本,书摊在屋子里,就像獭摆放鱼的样子,因此被人取了一个“獭祭鱼”的外号。
发现了唐人写诗的秘密,诗人不被神圣化、唐诗不被封入神龛,我们才能参透唐朝诗人如何获得创造力,包括诗人指涉历史的能力、对喧嚣社会生活的吞吐能力以及在此背景下呈现和构思自我的能力,这些对于特别需要创造力的今人来讲格外重要。
历史转折时期往往会给这个时代的诗人提供很多的可能性和素材,考验诗人的创造力。安史之乱是唐朝的重大事件,生活在这个时期的诗人们也被卷入其中。王维已然固定下来的长安诗歌趣味和身份,使他无法处理这一重大历史变局;李白咏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豪迈诗句,应邀加入永王李璘幕府,最终走上了流放夜郎之途。杜甫在安史之乱前的长安文坛虽然活跃,但名气依然有限,他的诗篇甚至不能入选同时代的诗歌选本《河岳英灵集》。安史之乱发生时,杜甫却创造性地以关注现时现事的“当代性”诗歌书写参与了这一历史事件,他的诗里表达了复杂的时间观,既有自己的颠沛经历,又有当下和古代先贤的坎坷,个人时间、自然时间、历史时间三个时间相互交叠。钱锺书因此把杜甫视为中唐以后众望所归的“大诗人”,王维与他相比,只能算“小的大诗人”。
安史之乱也是解码韩愈作品的一把钥匙。韩愈在思想领域提倡回归儒家道统,在文学领域发动复古运动,反对唐宪宗迎佛骨,冒死上书《论佛骨表》,原因是他认为释迦牟尼也像安禄山一样是异族。这样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既肤浅又可笑,但若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就会发现,韩愈所有的主张都源自安史之乱给中原民族带来的切肤之痛。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与其说隋唐是学术思想发达的时代,不如说隋唐是文艺发达的时代。”西川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唐朝是诗歌的时代,但诗人迭出却也让唐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
汉代有陆贾、贾谊、董仲舒、桓谭、王充、王符,宋代有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李觏、张载、朱熹、陆象山,明代有王阳明、李贽,明末清初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唐朝的佛经翻译和史学思想成就高迈,但没有出现过思想家。“唐人感受世界,然后快乐和忧伤,却并不分析自己的快乐和忧伤,冥冥中唐人被推上了抒情之路。”在西川看来,虽然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喜欢动脑子而不仅仅是抒情,但都是灵感式地思考问题,不成系统,称不上思想家。西川认为思想的品质势必影响写作的态度,因此当代写作不必回到唐朝,今天的诗人所要做的是以“容纳思想的写作呼应和致敬唐人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