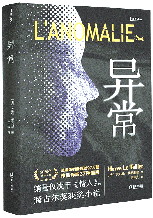
《异常》
[法]艾尔维·勒泰利耶 著
余中先 译
海天出版社
人类曾经认真思考过世界上是否存在另一个自己的问题吗?无论是克隆还是同卵双胞胎,都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个体,而非对单一对象的全盘复制。而一众时间穿越的故事,更是无稽之谈。似乎在人类世界,我们永远都遇不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备份,这样的模拟,是否真的只是梦中泡影呢?
“予谓女梦,亦梦也。”在开始叙述《异常》的故事之前,作者艾尔维·勒泰利耶引用庄子的这句话,表明了自己与读者同样的梦中人的立场。2021年3月,一架从巴黎飞往纽约的航班在穿越积雨云时遭遇了剧烈颠簸,所幸随后安全着陆。诡异的是,三个月后,同一架飞机载着相同的乘客再次穿过积雨云,在肯尼迪机场上空请求降落。通过这一情景的设置,勒泰利耶为我们模拟了一次对机组乘客的完全拷贝。
在勒泰利耶的描述中,宇宙像一台巨大的复印机,先被拿起的永远是复印件,随后原件才被捡出。然而,在原件出现前的三个月里,大难不死的乘客们并不知道真正的自己的存在,他们像从前一样生活,一样地做出选择。
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发生太多事情,当六月的自己终于降落在麦奎尔空军基地,有的乘客感情破败,有的已经自杀身亡。而跳过了三个月生活的六月的自己,将与三月的自己共享相同的样貌、性格,甚至社会身份。作家在四月死去,却又在六月突然继承了自己一炮而红的遗作;身患绝症的机长获得了选择另外一种治疗方式的机会;尼日利亚的说唱歌手打算和三月的他共同登台表演,而六月的杀手直截了当地枪杀了三月的自己。
勒泰利耶坦言,自己之所以创造了这么多角色,是为了拥有更多机会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小说中充满了科幻、恐怖、言情等多种创作元素,这不仅是对当今越来越严重的文化趋同的映射,更是为我们展现了普通人在面对着另一个自己时的诸多可能。身兼小说家与数学家的双重身份,勒泰利耶的创作不断体现着数学的特质,即无限的变化和可能性。
通过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与另一个自己碰撞出的火花,勒泰利耶想要完成的同样是一种模拟,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否被模拟,人们都活着,都有感觉,都会爱,都会痛苦,都会创造,都将在模拟中死去,留下一点点痕迹”,勒泰利耶正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结论来告诉人们,身份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种处境下的自己都正在拥有自己的人生。
《异常》荣膺法国最具盛名的龚古尔文学奖,作为乌力波文学组织的现任主席,勒泰利耶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我们从来不会期待像龚古尔文学奖这样的奖项。首先我们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其次我们也无法想象会获得这项殊荣。”
《异常》贯彻了乌力波文学组织一直以来的创作理念,即在自我设置的特定的束缚下完成文学创作,例如乔治·佩雷克的《消失》全篇不出现“字母e”,又如雷蒙·格诺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创作《一百万亿首诗》,《异常》中则是充满了与这些乌力波前辈们作品的互文。无论文学组织成员自己如何认为,赢得龚古尔都是乌力波的大获全胜。
乌力波直译为“潜在文学工坊”,旨在通过给创作加上各种各样的限制来挖掘文本之外的潜在可能。在乌力波的创作中,语言已经不再是工具,更是研究的对象本身。乌力波的作家们更像是数学家,而不是单纯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浓郁的后现代主义风格,解构传统的故事内核与内心意义,更注重文本本身,而往往缺少完整的小说情节。
在乌力波文学组织创立的20世纪60年代,这群作家旗帜鲜明地采用了反文学的创作方式,但作为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过分注重写作技巧,往往造成文学功能的缺失与局限,不能很好地体现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乌力波文学只有直面困扰人类社会的潜在危机,才能在数学之美上开出哲学之花。
在这一方面上,勒泰利耶的《异常》无疑是乌力波文学的一大突破,小说通过巧妙的故事背景设置,抛出了一个十分具有思考意义的现实问题,意在探索现实世界遭遇危机时发生的人性的动荡,其严肃的创作宗旨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和前沿人文问题把握,是一些内容怪诞的实验主义先锋小说完全无法企及的。故事的每一章用不同的行文风格进行写作,其实同样是对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困境的一种模拟。局部战争,暴力事件,伦理问题,贫富差距;人们素质低下,狂妄自大,同一阶层内部的人群更是分裂对立,缺乏共识,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如此阴郁的氛围之下,我们还拥有未来吗?
现实中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让人们觉得,世界局势紧张恐怖,人类社会前途堪忧,作者在影射之后,将这一问题提升到了别样的高度。
叙事之外,作家不但通过书中人物的口吻阐发了他对当前政治、生态、科技、社会的看法,更借由写作发出终极疑问:究竟什么才是人类的生存本质?
针对这一问题,作者在书中留下了疯狂的设想:“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充满幻觉的时代,每个世纪不过是大型计算机处理器中的千分之一秒?死亡到底是什么?一行代码上简单的‘结束’二字?抑或是其他?”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宇宙是真实世界的其中一份拷贝,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只是虚拟的相机底片中微不可查的一道数据流,我们所见的真实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洞穴中人偶跳动的影子?抑或者我们以为沉浸在周遭世界所组成的梦境中,实则我们才是某只蝴蝶梦中轻盈的幻象?
小说中杜撰出来的每个角色与自己的复杂关系,实际上真正意图探究的是人际关系,作者从个体的角度刻画人与自我、人与他人的纠葛,同时引申到人类群像,即描绘人类与身处环境,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本创作于人类世界面对疫情威胁之际的小说,也许正可以让我们思考,当“异常”发生后,如何面对自己、面对他人和世界。
小说背后蕴含的,是后疫情时代人类对天下一家愿景的重新探索,就算一切都是虚妄,在已经过去的嘈杂昨日与充满未知的美好今天,我们都选择继续前行。重要的不是我们如何存在,而是在我们存在的当下,我们的心中都充满着美好的愿望,以自己的方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