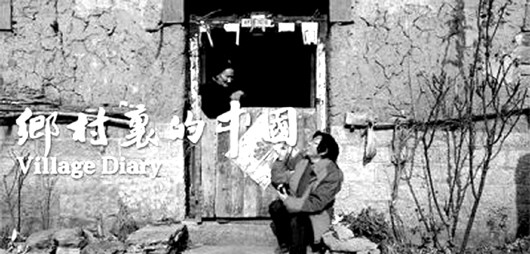□本报记者 魏新丽
“我觉得亲情和乡情是相连的,乡村就是爹娘的爹娘。”焦波被公众所熟知,第一次是因为摄影展《俺爹俺娘》;第二次是因为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在他四十多年的摄影经历中,爹娘和乡村是最重要的主题。亲情和乡情是一脉相承的,焦波曾说,前三十年拍爹娘,后三十年拍乡村。作为一个城市农民,他一直在这两者之中寻找渐行渐远的乡愁。
为父母拍照三十年
焦波今年60岁。42年前,他拿起相机给爹娘拍照的时候,爹娘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他用了整整30年时间,为爹娘拍了12000多张照片,录了600多个小时的影像。
7月30日上午,在省图举办的“大众论坛”上,焦波又讲起了自己爹娘的故事。去年是父亲的100岁诞辰,他把给爹娘拍过的片子重新编纂成了一本书,配上了自己的散文。父亲是个老木匠,早年读过私塾,喜欢念诗,大男子主义,说一不二。母亲大字不识一个,缠了小脚却能走得飞快。1.41米、35公斤的她生养了八个子女,其中四个夭折,剩下的四个里,她最疼的是那个脑子不好的傻儿。
焦波在影像中记录了父母琐碎的爱情。父亲锯木头的时候,母亲自然而然帮他扶住,母亲生病的时候,父亲低头亲吻她的额头。当然,他们也会为了几十块钱的随礼钱吵架,互相生闷气,过了没多久又和好如初。
一段一段,焦波一边放着电影,一边细细碎碎说着父母的故事。说到动情处,他哽咽起来。这些片段他反复看过好多年,但依然能够动情。
焦波父母的最后几年,是在快门的声音中度过的。“拍照对他们来说,是件幸福的事情。”儿子第一次拿着相机对准他们,他们还不好意思,有些扭捏。到了后来,只要是给他们拍照,他们都很开心。“问他们哪张最好看,爹娘说,都好看。”
焦波是个大孝子,爹娘在时,每个月必须回家一次。“不回去我受不了,母亲也受不了。孩子想回家看父母,会有借口的,再忙也有时间。”那个时候他在《人民日报》工作,全国到处飞,但是就在出差途中,有空他就会折返回去,看看老家的爹娘。
挽着裤腿的城市农民
讲座上的焦波穿着休闲随意,戴着常年不换的黑框眼镜。嗓门随父亲,很大,还带着乡音,脾气则随母亲多些,很温和。虽然已经是大城市的人,但在他身上,还能看到一些农民的品质,比如说,实在。
“我依然是个城市农民。”焦波对自己这样定位。在拍摄《乡村里的中国》时,焦波都不需要跟村民磨合。拍第一场戏,村民就跟他说掏心窝的话。因为他就像一个农民,到那里拉着村民的手,跟他们说话,一切都很自然。“在我眼中,老大爷就像俺爹,老大妈就像俺娘,太熟悉的感觉。”
焦波离开农村时才十八九岁,先是淄博,又去北京,现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他所见到的世界已经非常广阔,但从本质上,他依然是从博山小山村的泥地中长起来的农民。
“在北京22年了,情感还没有完全融进去,内心也不想完全融进去。我不想放弃我身上农民的东西。”年轻的时候,焦波怕被说是农民的儿子,他现在却很骄傲。大家问他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山东农村的,我爸是农民。
他依然保留着很多农民的习惯。比如说卷裤腿。在村里的时候,干活累了、热了,农民喜欢把裤腿卷起一截,凉快。焦波到现在依然这么做。这些行为被人说不像城里人,但对焦波来说,城里人的身份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
更何况,现在的他,待在城市的时间并不多,“一年三百天以上在农村。”他说过,前三十年拍爹娘,后三十年拍乡村。今年,他一直在持续拍摄《乡村里的中国》续集。今年打算出四部,在曹县,在宿迁,在宜宾,在菏泽,他在不同的农村中转来转去。
回不去的“土味”乡村
不过,乡村毕竟早已与他离开时大不相同了。
2002年的时候,焦波在村里干了一件大事,他把全村1000人组织到一个厂里,然后用相机给他们拍了一张全村福。十四年过去了,焦波却发现,想再拍全村福很难很难,“他们很难再聚集起来了。”
在中国乡村的迅猛发展中,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焦波能感觉到乡情的急速流失。“很可怕”,他不断用这三个字形容这种变化。“可怕的不是乡村面貌的改变,而是乡村道德的流失。”
邻里和睦的氛围越发淡了,同样淡薄的还有乡村里的亲情。“很多年轻人在外打拼,无暇顾及留守的父母。”经济大潮冲淡了人的亲情,焦波直观感受到了农村越来越严重的道德缺失现象。他亲眼所见,有的家里好几个女儿为赡养一个老人打得不可开交。“从这家撵到那家,从那家撵到这家。”他的一个婶子,曾经一个月只从儿女手中得到十块钱的赡养费。这令焦波感到寒心。
每到一处,焦波仍会持续不断地宣传他赖以成名的《俺爹俺娘》,这种执着被他赋予了新的功能,他要通过这种方式,唤醒乡村社会里承续自传统的孝亲文化,“把孝文化继续发扬光大,来挽救农村的道德流失。”
焦波的摄影和文字都有浓厚的“土味儿”,但给他的图片和文字打上烙印的乡村却在迅速消失。迅速起步的城镇化,越来越多的农村正按照城市的模样改造。对此,焦波多有不满,在他眼中,门对门户对户的四合院,不仅是建筑物,还代表了一种乡村的生活方式:不像楼房一样封闭隔绝,乡亲们有来有往,关系融洽和谐。
“我们老村子千万不要把之前的老房子都平了,孩子想回去看看都不行。”他有点迫切地呼吁。“我们已经找不回记忆中的乡愁了,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不是说一味盖楼,把他们撵到楼上去,就叫发展啊。楼房有四合院舒服吗?”
回来种树吧
有评论说,焦波的摄影和文字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民间记录,一种现场表达。“他挽留了那些细微的、被忽略的人和生活,让我们回望的目光有了着落。”这位用镜头传递乡间泥土芬芳和乡土情感的摄影家,在壮年时,最向往的也是城市宽阔的水泥大道和无限机遇。2004年,母亲临走的时候,跟焦波说,“回来吧,回来种地吧。”正值壮年的焦波,在外面打拼得正起劲,哪能回去呢。
直到母亲真走了,焦波才日益体会到一种悔恨。“就觉得自己当时太死心,太自私了。换成现在的我,说什么我也得回去。”
2008年,焦波回老家,包了一千亩山地,开始种树。银杏、国槐、枫树、核桃……他选的都是长寿树,“我这辈子得不到它们的好处了,但是我想把绿色留给乡亲。”当然,他也希望这些树能永远陪着黄土之下的父母。
焦波会亲自扛着锄头翻地,离开故土几十年,干农活倒也不觉得生疏,只是体力不如以前了。漫山遍野的树,寄托了焦波对故土和亲人的思念。“乡愁是一种感觉,是童年的一种记忆: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小路,但更多的还是人,爹娘,乡亲。”
有人说,“俺爹俺娘”,温暖妥帖,如一袭老棉被,温暖我们经久的岁月。这并不是焦波一个人的境况:回忆、童年、思念、老家、乡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里夹杂着越来越多这样的声音表达,即便是完全在城市里长大的新一代,也开始表现出对田园和乡村的向往。
“我觉得亲情和乡情是相连的,乡村就是爹娘的爹娘。”焦波知道,没人能阻止乡村的飞快变化,但是他希望能用相机记录这种变化,把曾经的记忆留存在影像中。就像他以前想用相机留住爹娘一样,他也在用影像留住乡村,“不管怎么变,我都能在片子里找到它。”
2012年,焦波回到家乡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用373天拍摄了一部记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这个只有167户,484口人的小山村,至今依旧保持着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干净的民风民俗,“老百姓的眼睛都是相对干净的。”在《乡村里的中国》里,焦波围绕村主任、老杜和磊磊三个人,为我们勾勒出了乡村的真实图景。片子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播放量达4500万。
接下来,焦波有个主意,想在老家的村子里搞一场电影节,组织乡村电影的评选。他想选的,都是那些讨论亲情和乡情的电影。在一些村子里,农民憨厚、淳朴、执着、热情、任劳任怨的品德依然留存,他希望未来的农村经济发展再迅速,也不要丢掉这些风俗人情。
“山水依旧,人情依旧。”这是焦波理想中乡村的模样。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