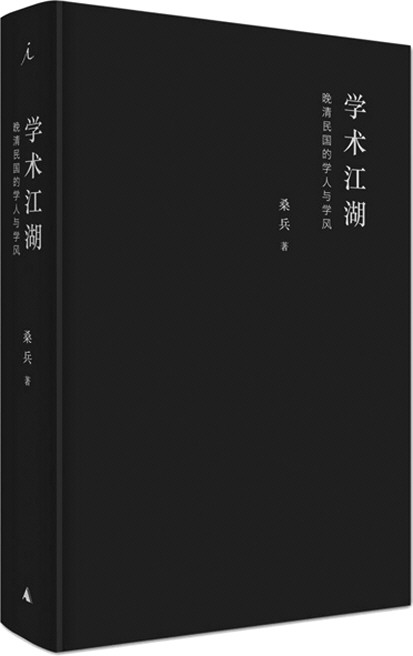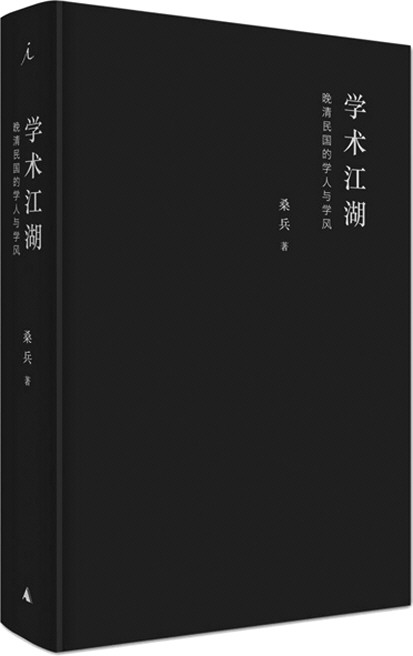
《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桑兵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桑兵
大学老师是否只需要讲课
蔡元培当年执掌北京大学,实施多项重要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教师不能一味照章讲授,必须有专门研究。
经过努力,北大里面只会照本宣科讲课的中外教员少了,教员必须做研究,并且不断将研究所得带入教学,尤其要言传身教,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研究引发学生自动研究的兴趣,进而加以引导。离开教员的研究,这一切都谈不上。
大学教书,教师有学问,怎么教都行,没有学问,怎么都教不好。传声筒留声机般的讲授实不可取,即便用心教学,没有研究作为基础,也只是将教科书或讲义的现成知识讲得好听而已,甚至为了吸引听众而不得不讲些哗众取宠的横通之论。
试想,老师不做研究,没有学问(这与发表与否、发表多少论文未必直接相关),如何能够教学生学会思考和研究?那些老生常谈和夸夸其谈,多半都是误人子弟。学生学不到东西还是小事,将学生教到不能再教的地步,才是害人不浅。
即使学生喜欢听,也不等于就不是灌输固定知识。以学生喜欢与否作为教员讲课好不好的尺度,看似外国经验,却未必先进。虽然私立大学开课吸引学生与收费相关,对于粉丝无数的讲授者必须另眼相看,却也未必是普遍准则。
曾经作为国联教育考察团成员来华考查教育的陶内著书,所指出的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学生听讲太多,考试太多,自修太少,与教员接触太少。教员则每周讲课钟点太多,兼课太多,教材过于利用外来的。顶坏的教授不过重演他们在国外所听的讲演。学生所读书本也只重知识的灌输,脱离中国的实际和学生的需求。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的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周培智谈及英国各大学教授历史的状况:“据云,学生每学年所选课程不过四五种,教授讲演亦甚随便,并且所讲甚少,非把某种历史全部讲完,全在使学生自己研究。教授但指定范围,至历史材料组织方法以及种种意义,教授全不指导,全由学生自己发明创造。盖中国教授方法在灌输知识,学生是被动的;英国教授方法在养成能力,学生是自动的云云。”
朱希祖闻言感慨道:“如英国教授方式,非学校图书馆设备完善,历史参考书丰富,其他都市图书馆亦藏书丰富,可以补学校之不足,则学生乃可自动。若南京各大学图书馆之简陋,则不特学生不能自动研究,即教授亦无法进步,其流为循环教育,而为灌输式亦势使然也。然能逐渐改良,亦属至要。”
英式的大学教育当然是独树一帜,或者认为缺乏系统性。尽管如此,如今大学乃至社会公共设施的图书设备相当完善,网上资源更是极大丰富,而海峡两岸大学的学期之长、课时之多,大体相当,放眼全球,仍然显得极为另类。不知为何,时时处处好与国际接轨的国人,唯独于此固执己见,以为上大学不是来读书,而是来听授。
可爱与可信,哪个更重要
教书与讲学并非一事,现在流行的讲学,并非宋明的旧惯,而是民国以来的新风,亦称讲座。前者以来学为对象,可以系统地循序渐进;后者面对驳杂的受众,上焉者择其精要,等而下之就只能投其所好。因为对象和程序不同,讲座既无法系统传授,也不能过于精深。
公开演讲之类,讲者与听众讲台上下随时互动,必须简洁明快地刺激后者的神经,每每将听众不懂、自己也未必知道的东西讲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若以治学的严谨态度,有太多的曲折、限定、保留、或然,则兴趣并不在此的听授者很难耐得住性子。若是一味以大众为言说对象,固然容易满足其自得欲,却也是学术停滞的表征。
明道之学与横通之学的差别不但表现在形式上,大学的普通基础教育,若仅仅以传授知识为目的,也与演讲大同小异。章太炎的国学演讲,王国维、陈寅恪在清华的教学,都因听授者范围、层次的不同而效果迥异。
钱穆自称当年在北京大学讲课极受欢迎,可惜缺少佐证,而且钱氏的无锡口音,一般人不易听懂。以其晚年在台湾讲演必须口译看,尽管早年北大的江浙籍学生为数不少,要全听懂也不容易。
朱希祖就有过教完一学期课学生连其所讲朝代人物都不清楚的故事,而朱氏的海盐话与钱氏的无锡话在其他地方的人听来,难易程度当在伯仲之间。所以张中行虽然将钱穆列在北大教授善讲的前三(胡适居首,钱玄同次之),却也坦言其乡音太重,致使听者常常误会。
更有进者,课讲得好听与讲得好往往是两回事。好听与否,全在受众的现场感觉,听众层次有别,反应自然不一。能够激起现场听众普遍共鸣的,大体是感官刺激的结果,绝不可能是须经理性判断的高深学问。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上课,虽然一再降低标准,选课者仍然难以承受。而陈寅恪之所以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变换角度看,也就意味着学生虽然听不懂,少数外校的高才乃至教授慕名而来,却能够满载而归。
民国以来,大学乃至社会上逐渐盛行讲学,流风所被,上课也以讲学为范型,课堂之上放言无忌的高论,不少是浅学者的妄言臆说。真正会教书而不是专讲教科书,尤其是能够从目录版本入手教书的,已是凤毛麟角。
1928年4月7日,清华国学院毕业任教于南开的陈守实“无聊中阅胡适《读书》一篇”,议论道:“此君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此意颇可玩味。胡适的水准至少当在一般之上,其讲授好听的程度还列于首席国立大学的第一,则普遍而言大学的讲课在通方之士听来岂非破绽百出?反之,若非绽论甚多,就很难讲得好听,高明之士滴水不漏的讲授,小夫下士听来索然无味,难以承接。
借用王国维“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一般而言,讲课让学生普遍觉得好听,大抵就不大好。因为学生大都只能凭感觉,不足以下判断。大学听授,若是可信逐渐可爱,则是提升收获;反之,若可爱日益可信,则多为误入歧途。
过于从形式上看重课堂讲授的灌输式教学,作为纠偏或有必要,作为理念则大可不必,且存在严重隐患。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大学教学就已经提倡专门化,鼓励和吸引本科生进入研究状态,效果如何姑且不论,理念应当是可取的。大学的教学,应当重在提升学生的能力,使之能够听懂讲得好并且逐渐觉得好听。
(摘选并整理自《学术江湖: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