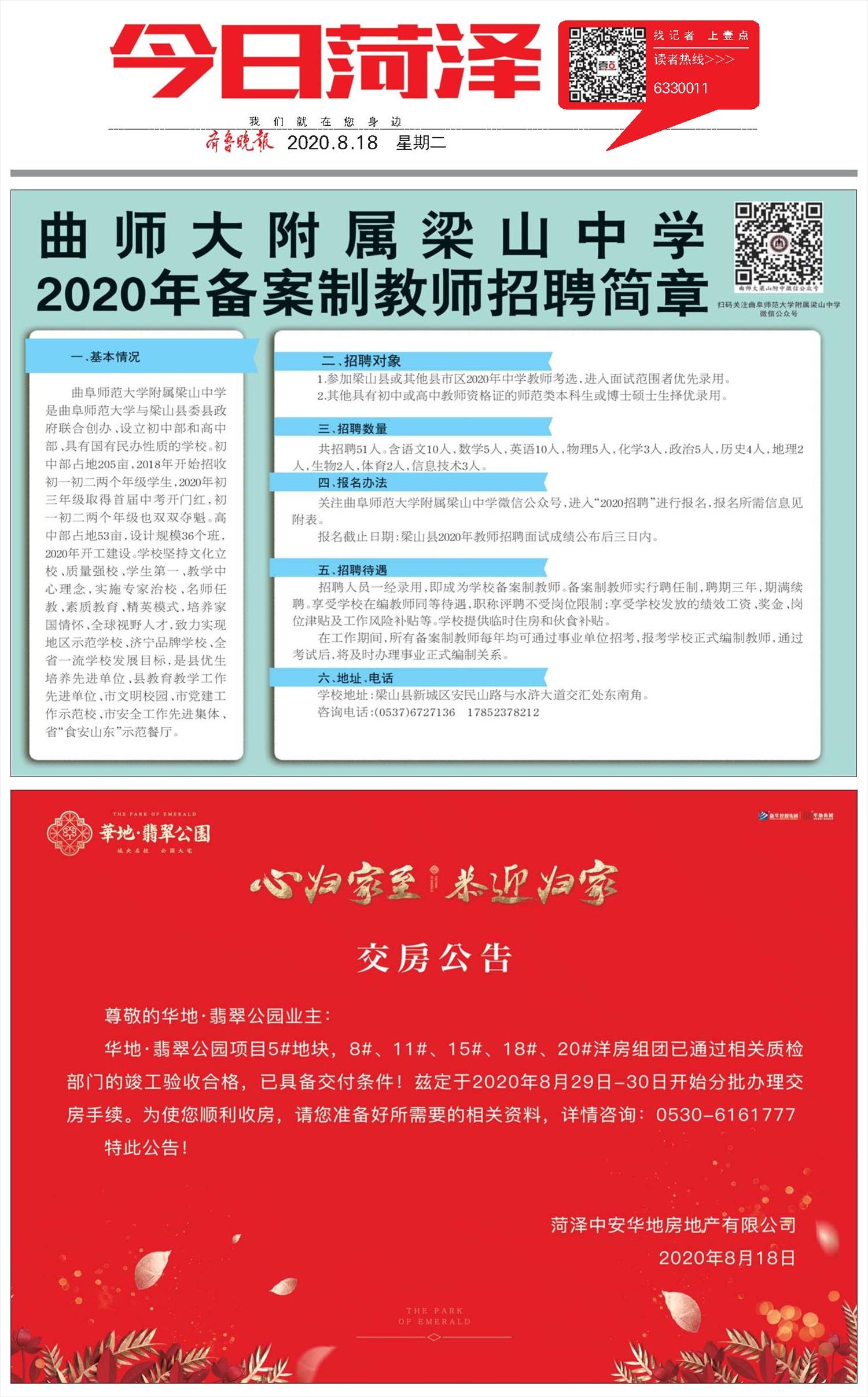□刘恒杰
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言谈时会不时地冒出一句半句或夸张或比喻的话来,极为形象生动又恰当地表达出了她要说的意思,别人听了也都非常明白。每当回忆起母亲,我常常觉得,她的许多话使教了十几年中学语文、后来又在机关里从事文字工作的我自愧弗如。
茶水能用筷子敧住吗?可母亲就能想得出来。
有一年元宵节,我回家看望母亲。我和母亲围坐在小铁炉边,听母亲东一句西一句说着村里人家的情况。母亲突然说:“胡同口你小脚大娘正月初八过世了,九十五岁。”
我说:“小脚大娘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吗?”
母亲叹了口气,说:“初八那天早晨,她起来喝茶,喝了一碗就跌倒了。初一她还迈着小脚过来看我。她那么好的身子,谁想到就那样走了。”
我说:“那小脚大娘从年轻时就喜欢喝茶。”
母亲说:“她早晨起来头一件事就是烧上一铁壶水,泡上一瓷壶茶。好天的时候她就把她的小茶桌摆在自家院子里的枣树下。她喝的那茶,就是两三块钱一斤的老干烘棒子。抓一大把放在茶壶里,泡出来的茶水酽酽的,又黑又亮——那茶水啊,能用筷子敧住。”
茶水浓,浓到能用筷子敧住——这也真够夸张的了。
我们村东北有一个叫五叉沟的地方,那里曾有我家的一小块自留地。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午后,母亲牵着四岁的我向地里走去,去看看地里的小麦熟透了没有。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到那块麦田去。被太阳炙烤的道路烙着我光着的脚丫。
刚出了村子,我就抬头问母亲:“快到了吗?”
母亲说:“快了,前头就是。”
又走了一会儿,我又抬头问母亲:“快到了吗?”
母亲还是那句话:“快了,前头就是。”
我说:“那太阳怎么那么热啊,那路怎么那么长啊。”
路边有一棵杨树,母亲领我去树阴里歇一歇。
我突然听母亲说:“路有多么长啊,就像想儿的娘啊;筷子多么长啊,就像儿想娘啊。”
母亲的眼睛看着远处,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那时,我不懂,但这句话却印在了我的心里。其实,那块麦田,离村子不到三里路。
那年,在我离开家乡去外地读书的那天,一家人围在一起吃中午饭。母亲突然说:“去了,不要想家。”
那时我心里充满了对远方的向往,怎么会想家呢。
当我背起行李,迈出大门口时,我听见母亲说:“娘想儿,有路长;儿想娘,筷子长。”
路有多长?天下的路没有尽头——那是母亲对儿子长长的思念。走遍天涯海角,也走不出母亲的牵挂。
是一个下午,一个暑假里静静的下午。
我在老宅的西屋里看书,母亲在北屋里和本家的一位嫂子说话。那位嫂子已寡居多年。那位嫂子在那年春节后为她唯一的儿子娶了媳妇,可三个月以后就分家了。分家了,但还住在一个院子里。
我听见那位嫂子诉说着儿媳妇的不孝。说儿媳妇日上三竿了还不起床,说儿媳妇包了水饺从来不端给她一碗,说儿媳妇从来不让儿子帮她忙忙地里的农活。那时,农村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后来,我听见那位嫂子长叹了一声,说:“大婶子,这真是‘长尾巴狼,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撵到大街上,媳妇背到炕头上’。”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母亲说:“其实当娘的啊,一个甜枣就吃不了。”
我知道母亲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当父母的对子女特别是对自己的儿媳妇,没有多少要求,哪怕就是一句嘘寒问暖的话语——就像一个小小的枣儿,老人们也会万分感动。
有一年秋种,大旱。
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走到雪野湖岸上时,看见湖里已经没有了水,湖底裸露,皲裂。回村后才知道,村里十几眼机井都抽不上水来,全村人几乎都去村西龙王庙求雨了。我抬头看看天,一丝儿云彩也没有。
吃晚饭时,也去求雨的母亲回来了。我说:“不能光指望老天爷啊,要不,咱连夜用小推车向地里运水,今下午我还从咱家压水井里压上来两筲水。”
母亲说:“好几亩地呢。那点水能有啥用?还不够研墨的呢。”
说某个人好占便宜,母亲会说:“那个人就知道勺子外头搲饭吃。”
说某个人成天有说不完的话,母亲会说:“那个人啊,一天到晚满嘴里跑舌头。”
说某个人说话干脆利落或铿锵有力,母亲会说:“他说话,唾沫星子掉在地上都砸个窟窿。”
村里的人去世了,脸上会盖上一层火纸,母亲就会说:“咱庄户人的命啊,就是一张薄薄的纸。”
……
母亲说这些话的时候,从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