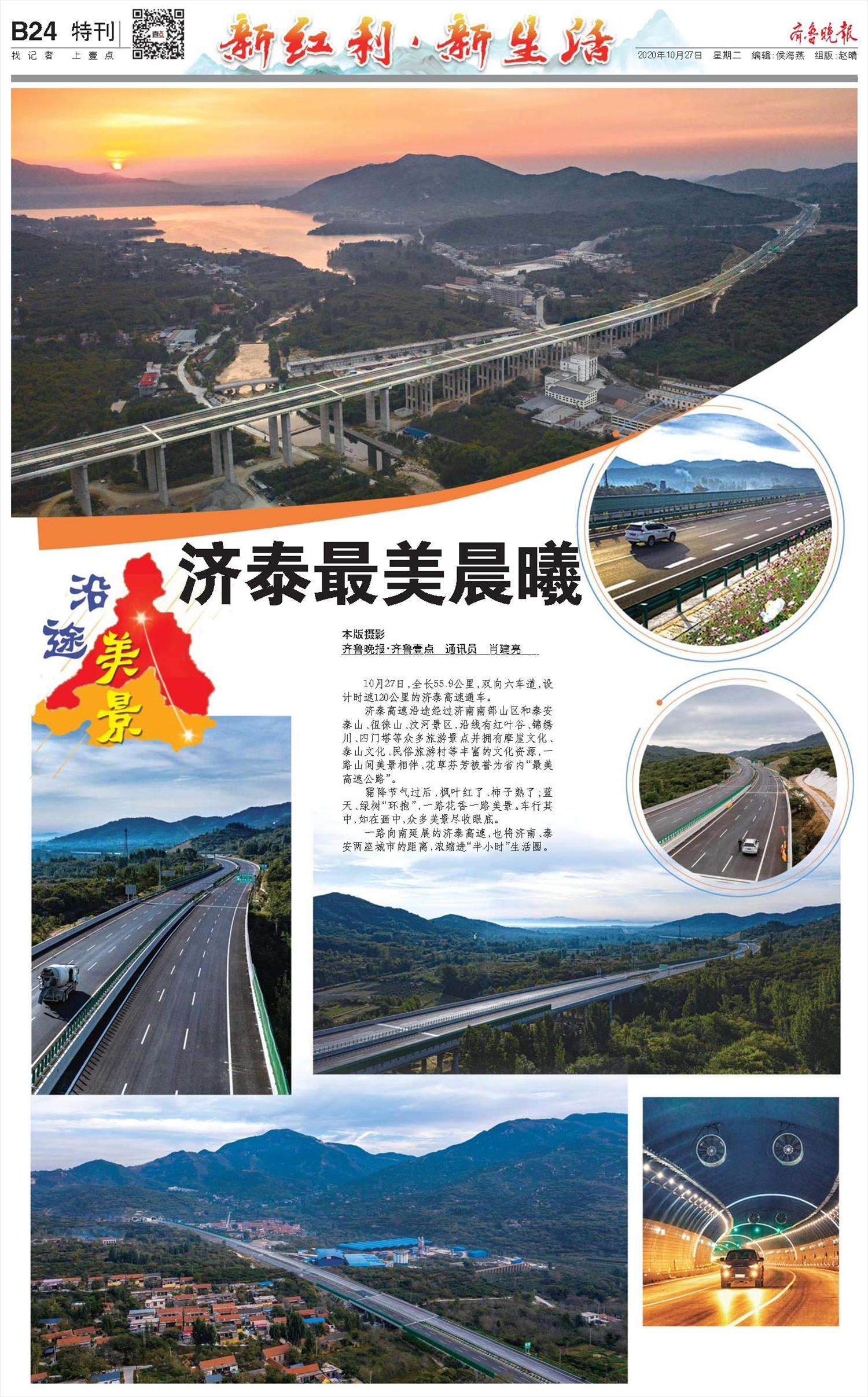吴伯箫先生
□张维明
吴伯箫先生是我非常喜欢和尊敬的散文家、教育家。上中学时曾学习过先生的几篇文章,后来当中学语文教师时又给学生讲解过他的文章。197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增订再版先生的散文集《北极星》。当年6月1日,我很幸运地在县新华书店买到了这本书,回家后挑灯夜读,一口气读完。全书25篇文章中,不仅有《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等比较熟悉的篇章,还有我第一次读到却倍感亲切的《一种杂字》一文。
先生在文章中说:“我的故乡莱芜,在封建社会一般人家的孩子念书,只求识几个字,能记记账,写写春联。启蒙书就是三本:《三字经》《百家姓》《日用杂字》。”“因为小时候念过家乡的那种《杂字》,印象很深,有些字句背诵起来感到很亲切,就很想再找来翻翻。早些日子写信到故乡去找,回信说这种书已经不大有人念了,急切找不到。感到很失望。前天忽然从老家寄来一本,说是辗转经过几道手才得来的。我真说不出的高兴。像渴了喝水一样,一口气念了两遍。”
接下来,文章对《杂字》的内容做了一些简要精到的介绍和评论。如:“这种《杂字》是五言的,叫做《庄农日用杂字》。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像某些《杂字》那样,把一些单字分类凑起来,讲不出什么道理;而是组字成句,句句都有比较完整的意思。譬如头两句‘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意思就很好,很足以带动全书。”“这种《杂字》共四百七十四句,两千三百七十字,是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桩农事又一桩农事接着写的。中间也写到饮食起居、男婚女嫁。有的还写出了事情的简单情节,相当生动。”
最后,先生特别强调:“这虽然不是名家的名著,但终究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个不太小的地区流行过的启蒙书,湮没失传总是可惜的。”“真希望故乡哪个人民公社能够采用这种《杂字》作组织农民学文化的课本。如果翻印的话,可以配上插图,有的难字还可以加注音、解释。当然,为了使《杂字》更切合实用,根据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情况,修订或者改编那是更需要的。”
读完全文,一股喜悦亲切的暖流在心中激荡。因为先生所说的《庄农日用杂字》,作者马益著,乃是我们临朐老乡,我很小就听到那些只念过几年书的父老时不时就念诵起《杂字》中的某些章句来。
据《临朐县志》等文献记载,马益著,字锡明,一字梅溪,临朐县胡梅涧村人,大约生活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他天资聪颖,十岁能文,及长博学多闻,间习杂家艺事,无不精妙,年逾八旬著作不辍,遗稿甚富,有《四书声韵编》《诗韵撮要》等十多种。至于这部流传甚广的《庄农日用杂字》的写作,还有个故事。乡间传说,马益著虽然饱读诗书,却怀才不遇,屡试不第,只于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得岁贡,不仅遭乡里士绅讥讽,连父亲也斥责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懂庄户活,一生何以为计?马益著赌着口气,一夜工夫写成《杂字》。此文一经问世,乡里便相互传抄,风行一时。后来各种书局又广为翻印,《杂字》成为山东及周围较大地区乡村儿童的启蒙读物。
《杂字》写的是农村生活,生动活泼,易记易懂,朗朗上口,很是普及。记得小时候看生产队社员开春到家里栏圈出粪,两人抬着一筐沉重的粪土,其中一人走着走着说不定就背诵起《杂字》来:“开冻先出粪,制下镢和锨。扁担槐木解,牛筐草绳拴。抬在南场里,倒碎使车搬。”另一人不由自主地就接上话头:“粪篓太也大,春天地又暄。只得把牛套,拉绳丈二三。肚带省背鞅,搭腰四指宽。二人齐上袢,推了十数天。”
麦收时节,在打麦场上,有时也会听到正在翻场的老农即兴哼几句《杂字》中的句子:“明日把场打,麸料牲口餐。套上骡和马,不禁碌碡颠。耙先起了略,刮板聚堆尖。扫帚扫净粒,伺候好上锨。迎风摔簸箕,扬的蛾眉弯。若遇风不顺,再加扇车扇。”
辛苦劳作时,哼几句《杂字》,就像唱几句山歌一般,不但活跃了气氛,减轻了疲劳,还常常博得众人叫好。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读过《杂字》,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听得多了,竟然也零零碎碎记住了不少句子。
记忆中,还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画面:冬夜,生产队的牛棚里,挤在几个成年人之间,围着火堆烤火取暖。火熄了,就有人用火棍扒拉着灰堆,以助其燃尽。有人说起春节将近,有人说起腊月大集,有人诉说起收成不好,囊中羞涩……就听有人叹口气,念叨起《杂字》中的句子:“妮要坠子戴,小要核桃玩。一阵胡吵闹,令人不耐烦。好歹混混罢,哪有乜些钱。纵有几千吊,也是买不全。”是自我解嘲,还是自我安慰?大家都闷着不吭声了,火星映着一张张面孔……
我那时还不太懂事,但也隐隐约约感觉到《杂字》中的文字有一种神奇的魅力。
吴伯箫先生的文章写于1961年7月18日,他在文章中表示很担心《杂字》湮灭、失传。现在的情况比先生想的要乐观一些。其他地方我不清楚,在老家临朐,人们对《杂字》的保护还是非常重视的。就我所知,1980年3月,临朐县文化馆就将其刻版油印,装订成书。后来,新编《临朐县志》和县政协编印的《临朐文史资料》等书籍,也都分别载录了《庄农日用杂字》。2006年,《庄农日用杂字》还被列为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对该《杂字》的研究文章,也不时见到。
文友王兆亮先生很注意历史档案资料的收集研究,他收藏的清代、民国时期的这种《杂字》就有12种之多。前些日子,我欣赏了他收藏的这些《杂字》,有四种印象很深。一是恒文堂刻于光绪戊申的一种,名《日用杂字》,封面注明“朐邑清溪马先生著”;二是成和堂刻于光绪戊申的一种,亦名《日用杂字》,封面注明“朐邑清溪马先生著”;三是上海大成书局发行的,名为《绘图庄家杂字》,没有注明作者,纸张很差,开本不大,每页印刷40行,很是拥挤,这和当年吴先生看到的本子是同一个书局出版的,内容相同;四是安东(今辽宁丹东)诚文信书局印行的《绘图日用杂字》,印刷比较精美,可见《杂字》一书过去在东北也是很流行的。
近年来,随着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对乡土教材的发掘、编写越来越重视,《杂字》也进入一些中小学教育机构的视野。2007年,临朐县青少年学生科技创新教育实践基地曾印刷了几千本《庄农日用杂字》,还加了拼音和注释,“以供现大多不谙农事的后生们学习,并望对其有较好的教益。”虽然用心良苦,但据说效果一般。学生不用说,就连许多年龄不小的教师,面对《杂字》中一些农具、服饰的名字,也是茫茫然。毕竟,吴伯箫先生写作《一种杂字》至今,又是60年过去了,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农活和生产工具等变化也是非常之大的。
《杂字》作为教材,已经不太适合了,但是《杂字》一书创作编写的成功经验,却是值得借鉴和继承的。《杂字》深受群众欢迎、广为流传的根本原因不外是通俗易懂、紧贴社会生活实际、集中识字、韵文识字、乡土风味、易记易诵等,这不正是我们现在改革语文教学和编写教材的好范本吗?这不正是吴伯箫先生当年撰写《一种杂字》一文的初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