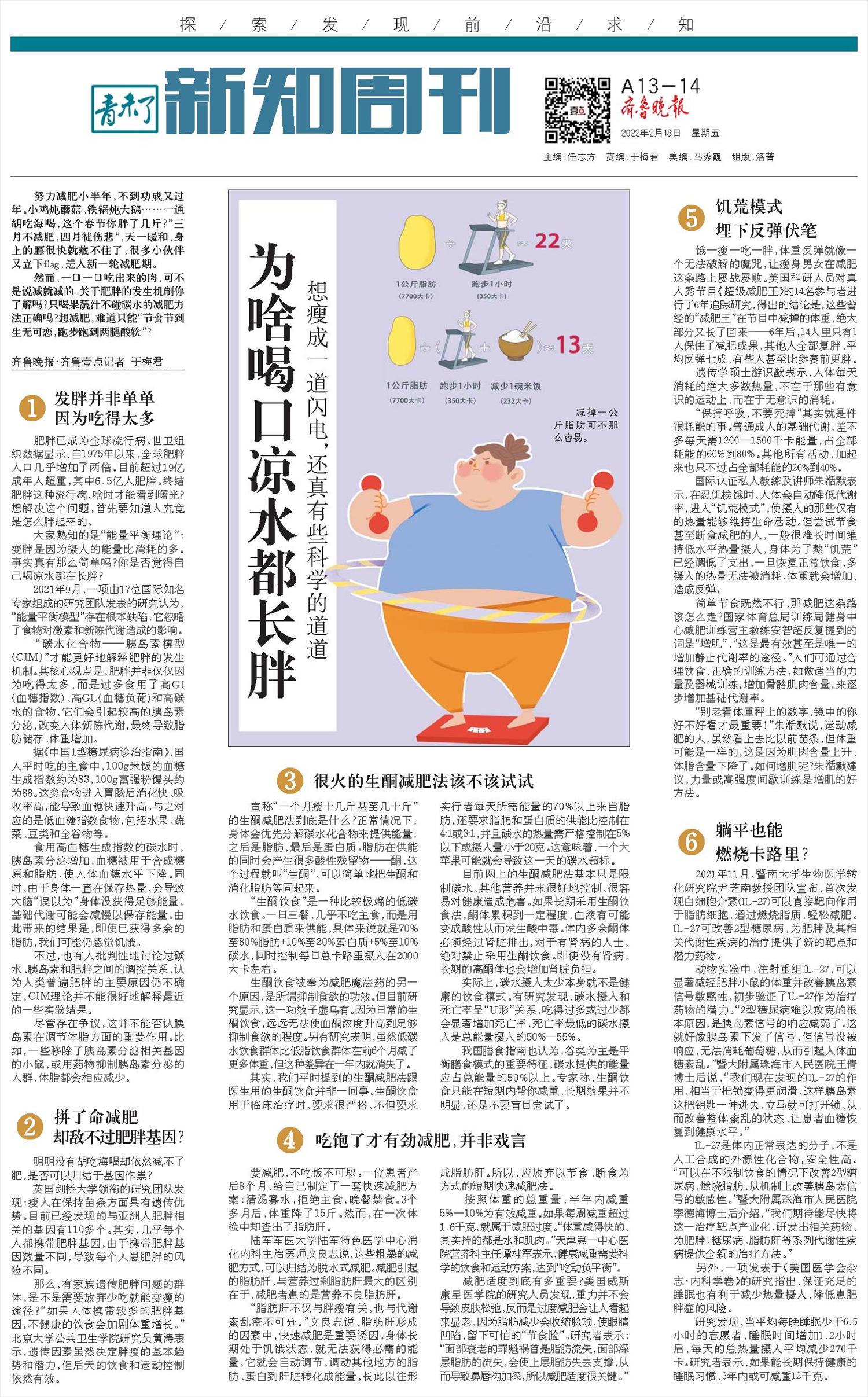□葛昌明
冬天的早晨,当我们还躺在炕上,窝在被子里时,母亲已经点燃了炉膛里的柴草。屋子里迅疾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待柴火燃旺,母亲把煤块掰碎丢进炉膛里。母亲跑过来将我们被子的一角掩实,不让我们裸露出来的肩膀着凉了。之后,母亲挑着水桶去水泉上担水去了,于是在我们匀称的呼吸声里,炉火旺起来,放在炉子上的锅里的水开始响起来。
在袅袅炊烟升起的地方,便有了岁月的温情,拾起了游子的衣襟。然而,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因为模糊的记忆和贫穷的生活,限制了我们收藏它的心情,往往把这些风景疏忽了,任它流浪在风的平原上。
金坪,这是一个在地图上可以忽略不计的村庄,这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村庄。周婶家用铁勺油炝葱花醋,就能香飘整个巷子;一声狗叫,一声驴嘶,都能辨清是门前芮家的还是屋后南家的。这里养育着七八家姓氏的百来口人,金坪——生我养我的故乡。
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大沙沟、小沙沟、榆树沟沟、沙渠湾、南仓沟、溜拉牌等沟沟岔岔走出来的王、卢、杨、芮、葛、罗、南等几姓人家,选中金坪这块地方,修房安宅,开田拓地,于是,有了金坪的村落。
从散居到聚居,村庄的形成,是基于群体成员(村民)共同的需要,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半坡人从原始森林到半地穴式而居,并非一蹴而就。然而,“金坪”,或许因其普通和微小,其建村的历史离我们并不太远,都存活在金坪每个人的记忆里。至于散落在金坪沟沟岔岔的人家,每一户都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传说。
庄户人家的意识很淳朴,早出晚归,耕田种地,养家糊口,却无意间赋予了“金坪”无限美好的想象。金坪,既没有“金子”,也没有壮阔的“坪地”。前临山,后依山。按理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满沟满凹光秃秃的,石头多,可耕的田地并不多。金坪切切实实是靠天吃饭的,然而,十年九旱,金坪,并没给予我们多少粮食。
苦难是鲜活的,记忆是悠长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坪的人们默默无闻地过着紧紧巴巴的日子。而随着他们的颠沛流离,或者走南闯北,金坪,这个村庄始终有二郎神的护佑,有皮影戏的陪伴,有社火会锣鼓家什的铿锵。信仰和生活的联结,自然结成一种朴实而顽强的精神,犹如巍峨的米家山,冬青夏翠,丰满着贫瘠岁月里或稀或稠的拌汤,体恤着他们的春夏秋冬,交织着他们的悲欢离合。于他们而言,即使日子过得很单薄,但总相信阳光总会照耀到他们的脸庞,温暖他们的胸膛。
一股从喜鹊沟引流下来的泉水,在庄子东南面经久不息地流淌,喂养着全村人及全村人的骡马牛羊鸡猪狗。泉水聚成一汪浅浅的涝坝,十天半月,浇灌着菜园子的几亩水田。
泉水很甜,故土难离。上世纪80年代末,要从金坪往灌区搬迁,多数人家一定要带上几壶金坪的泉水。但无论金坪的泉水怎样香甜,金坪依然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它可以蕴养我们对水的最原始的记忆,却满足不了我们果腹之需。
说走就走。搬迁,从干旱山区到提黄灌区。于是,金坪,这个在我们眼里还称得上繁华的小村庄,迅速解体,只剩下三四户倔强的人家,再就是一地残垣断壁。
我们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
沿着这样的思考,我们世世代代迁徙、繁衍、生活。或许答案不是唯一,但我们就这样努力地仰望着生活的蓝天。
马兰花盛开的时候,我们赶着一群驴在山沟里砍柴。冬天,男人们在钻夹墙的煤行里,在孱弱的煤油灯光下,在漆黑的世界里挑起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女人们则包裹着头巾,去拾头发菜。走街串巷的甘谷货郎来了,猪鬃换点点花馍的颜色,给孩子买几颗豆豆糖,置一把篦子、梳子,换一两件衣服,扯几尺花布。腊月里杀年猪,把左邻右舍都喊过来吃顿年猪饭,日子过得如此简单。
在岁月的长河里,金坪,它只不过是我们居住生活过的一个小小的村落。但终究将它的一山一水刻画在我们人生的坐标里,烙印在我们柔软的心底。一生一世,在或长或短的人生履历上,始终书写着这个简单的符号。它并不富饶,也非富有,却给了我们生的勇气与活着的希望。
灯光是一个丰满的形象,煤油灯是金坪夜晚的开始。同样在忽闪忽闪的灯光下,母亲在缝缝补补,或者趴在炕桌上拣头发菜,或者在给我们捉衣服上的虱子。也还是在那盏煤油灯下,父亲教我写过“大、小、多、少”“上、中、下”“马、牛、羊”“人、口、手”……
于是,在来来往往的旅程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起起落落的潮流里,在过去与现在和未来之间,金坪,它有形无形地漂泊着,让故乡的人在梦里牵挂,在记忆里寻找。
百十来口人的小村庄,有会打铁的,有会缝皮袄的,有会做木工的,有会画棺材的,有会打卦的,有会接生的,有会说媒的……技能和日子联系,手艺与生活贴近,可以稍稍让他们的日子与众不同,也因了他们的参与,可以真实地完成庄子上每一项重大工程,比如耍社火,到庙上求雨,比如修路筑坝,背砂压田,开渠引水,还比如每户人家的婚丧嫁娶,几乎全庄子人都在走动。这既是农耕时代变工互助之精神的传承,也是村民齐心协力具有的格局。
谁家的骡马走失了,小儿夜哭等等闹心之事,必有易人相求相解,至于上梁安灶,吊门起坟,禳灾祈福,金坪上的人小心而谨慎,拜二郎,访易人,恭敬而诚心,让平淡的日子,朴素的生活,长出热情的仪式,为瘦弱的岁月绽放出异样而绚丽的色彩。
春种秋收。麦子打了多少石,糜子打了多少石,在很长一段时期,这始终是金坪上庄户人家关心的中心。好的庄户人家有好的收成。我的小伙伴家里生活条件好,他常吃白面馍馍,我就想着用我的黑面馍馍换他的白面馍馍,他竟然乐意,我也很高兴。
水沟是块奇特的地方,有块滴水的岩洞,夏天的时候,走进那岩洞里,竟然还有冰棱子;水沟对面的沙滩,有成为化石的乌黑的鸟蛋;中台子全是压了砂的砂地,种着糜子,也有的种瓜;糜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偷吃糜子的鸟儿多,地边上插着的稻草人鸟儿不怕,我们就要去打鸟儿,看见麻雀快靠近糜子地里了,嘘——嘘——鸟儿便高飞在秋天的天空上。
寒来暑往,四季循序。金坪,带着股韧劲,绵延在岁月的河道上。简单,抑或简陋的小村庄,既赐予我们历数不清的苦难,也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快乐和幸福——金坪,我们拥有真实生命的所在。杏树园子的水结成了冰,我们穿着单薄的棉窝子在那儿溜冰;在灰堆上捡拾没有燃尽的炭块;在喜鹊沟里拾柴,夹墙里挖煤,鸦儿沟放驴,跟着沟沟里乾爷闹社火,站在大凹上伸长脖子看马场山的电视转播塔……
马尔克斯说过,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即便这样,我们记住了在金坪上的生活,虽然繁琐,但却一直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