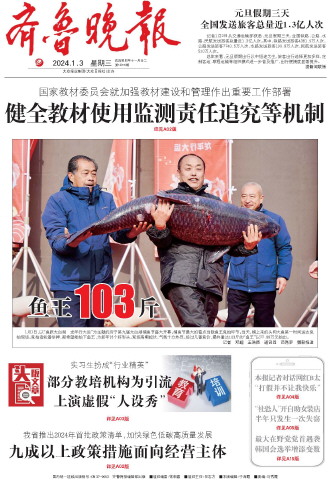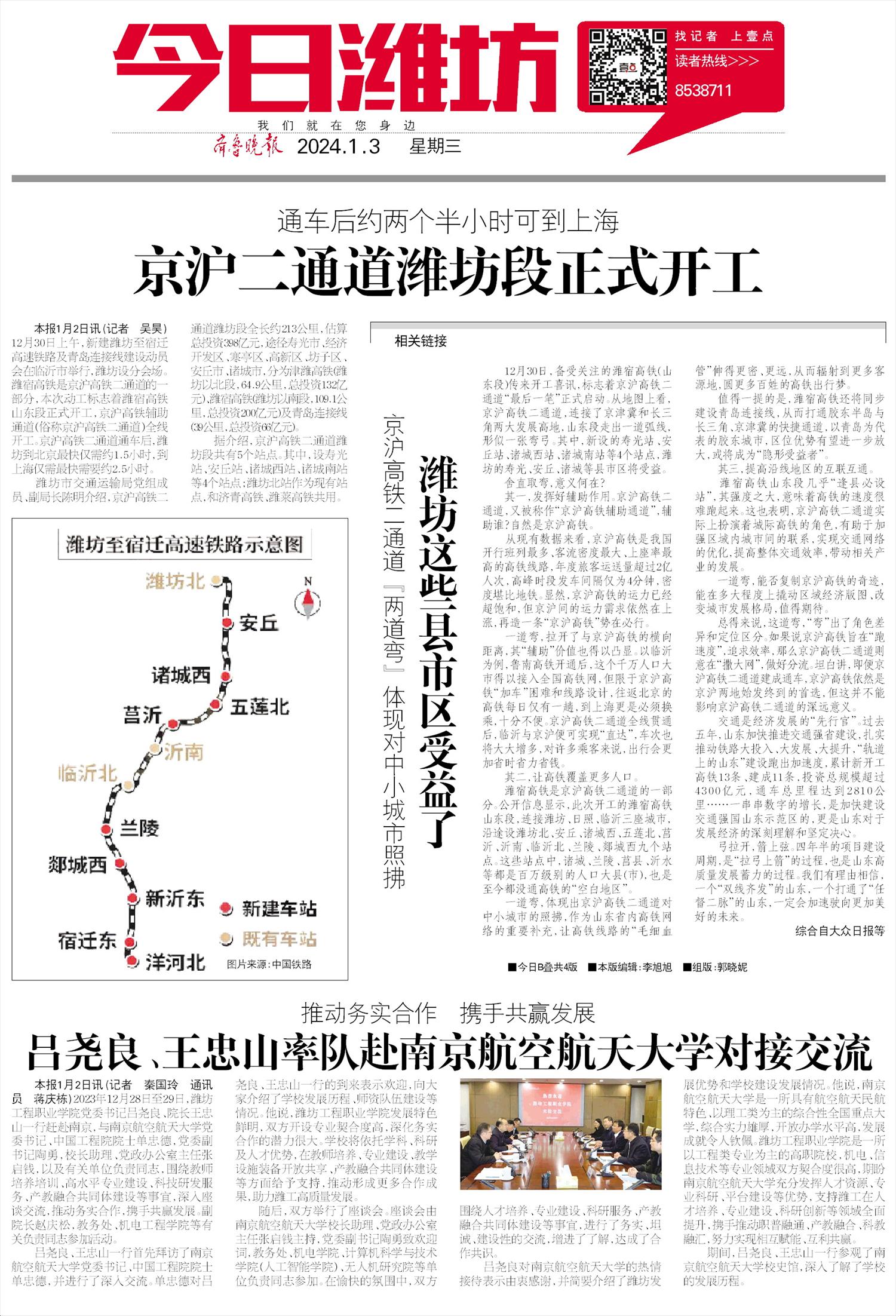□李怀宇
2004年6月中,莫言有广州之行。我意外得到消息时,也得到了莫言的手机号码,随即打过去。莫言爽快地说:“我现在就在南方书城,你可以马上过来聊天。”约半小时后,我见到莫言。南方书城办了一个读者见面会,场面并不热闹,记者更是寥寥。活动结束后,我们就坐在南方书城靠窗的一角聊天。刚谈了几句,我就发现,他虽笔名为“莫言”,实则出口成章,真不愧是“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近一个下午的时间,只要稍微提起话头,莫言便能说出一番让人舒服的话。
提到学者气与文人气的问题,莫言说:“我没有学问,所以没有学者气,我始终没有把写小说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是一个农民,现在依然把自己跟农民认同,所以就没有文人气了。我还是认为人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不仅仅在意识上当作是老百姓的一分子,而且从所有的方面感觉到其实我就是老百姓的一分子。一旦想到我是一个作家,就一下子把自己架空了,自己把自己摆在一个并不恰当的位置,比较难以让人接受,令人厌恶。”
当天晚上,南方书城宴设广州客村的一家潮州酒楼,我也受邀敬陪末座。记忆所及,偌大一个包间,同席只有四五人。莫言对潮州菜充满好奇,恰巧我是潮汕人,每上一道菜,莫言便问起菜品特点。“秋刀鱼饭”是一道平常的潮州菜,莫言尝后,连说:“秋刀鱼之味,秋刀鱼之味。”莫言少时家贫,总吃不饱,食量又奇大。“越饿越馋,越馋越饿,最后分不清了是饿还是馋。”他甚至吃过煤,而且觉得特别好吃,这让我大吃一惊。后来莫言把吃煤的故事写进了长篇小说《蛙》的第一章开头。
一席谈中,莫言十分随和。问起记者生涯的趣事,他很认真地说:“我也是《检察日报》的记者,有正规的记者证。记者所见所闻的故事,往往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我便笑道:“金庸也是记者。”
谈到当下一些离奇古怪之事,莫言的谈锋偶露峥嵘,但保有分寸,批评时事也显得相当谨慎。后来观其在公共事务上的行止与写作上的风格,“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也许是肺腑之言。
那天下午我们的长篇对答,莫言健谈而又得体。我第一个问题是:“大江健三郎曾公开表示对你惺惺相惜,认为你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如何看待作家与文学奖的关系?”
莫言从容道:“从学养、阅历和成就方面,我无论如何没办法和大江健三郎相比。我们有私人的交往,有些友谊,他对亚洲文学有殷切的希望,他希望有一种亚洲文学的出现,还有对中国非常深厚的感情,对我也有对晚辈的扶持的意思。关于文学的奖项,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副产品。一个人在写作,肯定不可以为奖项来写作,只能说是我写出的作品被这个奖项所青睐、所看中,有时候考虑得奖,反而得不了,对待奖项还是这种态度比较好,是写作出现后的偶然性现象。当然,得奖对作家有一定的好处,可以提高作家的知名度,在那一瞬间满足作家的虚荣心、自信心,也可以给作家带来一些奖金。我觉得文学奖尤其是给作家一个警惕:这个奖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终身成就大奖,几乎对这个作家宣布创作的终结,对我产生巨大的警觉。尽管我得到奖项,我应该立刻把它忘掉,重新开始。我记得在一份报纸看到一个可爱的年轻作家说:莫言已经得了某个奖项,他可以休息了。我觉得过去的莫言可以休息了,得奖的莫言还要更加奋斗,不应该让奖项变成阻挡自己前进的包袱。”
我又问:“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让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的风格。你的作品不停地对传统写法进行挑战,也借鉴了不少西方的技法?”
莫言说:“西方技法对我是一种刺激,激活我的记忆力,增长我的信心:你胆大,我比你还胆大。我对西方小说看得不多,一个作家看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从技巧上来说,确实也是有一种窥一斑而知全貌的现象。就好像《百年孤独》,我至今没有完全看完,但是我很清楚马尔克斯的语感,虽然是翻译家翻译过来的,但相信还是转达了原文的风韵。马尔克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也设置了一个陷阱,标杆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这种高度,陷阱就是你往他靠近,你就会掉下去淹没了,可能就有灭顶之灾。只有一个作家在个性化的道路上探索了很长的时间,取得一种高度的自信,自以为像一个武林高手练成了什么神功,可以跟这种功力对抗的时候,才可以面对面地写作。我下一步就是想跟马尔克斯面对面地写一篇试一下,看是打个平手还是一败涂地。”
当年我仍对莫言小说的故乡情结印象深刻,便问:“故乡山东高密是你写作的源泉。有人说,莫言的作品以写农村题材居多,没有学者气、文人气,因此至今还是一个‘乡土作家’,无法进入更高的层面。这话你是怎么看的?”
莫言说:“关于故乡的这个概念,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对一个离开了故乡二十多年的作家,故乡是我的精神归宿和依存。对故乡的想象是不断完善扩充,不断回忆往事,对故乡的回忆也是想象、创造故乡的过程。任何一个作家的童年记忆对他的创造都始终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是在不断比较,碰到新的事物时,总要拿些自己经历的旧事物比较,比较很可能调动童年时期对某种事物的看法。至于人跟自然的关系,善恶的道德观念,实际上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形成,后来肯定有调整,但这种调整更多的是在理性的层面上,在感情上是很难拔掉的。‘乡土作家’对我也不是贬义词,就像贾平凹说‘我是农民’一样,说我依然在乡土的层面上写作也不是一件坏事。所谓的乡土不是狭隘的乡村,每一个作家的乡土是他所寄身于其中的地方。对王安忆来说,乡土是上海,贾平凹的乡土是商州,实际上每个作家都是‘乡土作家’。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包罗万象,每样事情都写得很地道,那是受个人的经历局限的,但这种东西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手段来修正一部分。实际上,别人对我的评价是有很多意象化的,我的《酒国》、《十三步》是写城市的,其实我写城市、乡村各占一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只能写农村呢?”
莫言意犹未尽,更以前辈作家为例:“沈从文、茅盾无不以故乡为依存的。这些地区的小文人、小知识分子突然进入城市,像沈从文刚到北京的时候也是极其凄惨的,刚开始的题材也不都是写湘西,有可能是时髦的题材,但是他感到这些对他不利,在艰苦的情况下要在北京生存,要走出来跻身于文明人的行列,拿什么作敲门砖?只有回到故乡,从记忆里挖掘宝藏,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人生的感知,是非常原创的东西。一出来大家非常惊愕,与其他的作品完全不同,所以他就成功了。然后沿着这条路写一批湘西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他的创作生涯是很短暂的,假如他一直写湘西是不行的,他要发生改变的,他有些作品如《八骏图》等根本无法跟《边城》等相比,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在里面。他写湘西是一种炫耀:我就是让你们知道一下老子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你们这些北京、上海人不要跟我牛皮,没什么好牛皮的,你们神气什么呀,老子十五岁就杀人去了。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有炫耀心理,一种任性,不服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的东西我认为不好,我把我家乡的抖给你们看,你们所谓的英雄才子佳人,我们都有,而且比你们的精彩,跟你们的不一样。”
我向来欣赏作家不断尝试的勇气,便问莫言如何思考作家风格的定型化?
莫言答道:“我是特别怕成熟和拒绝成熟,一旦成熟就很难改变,刻意变化是要冒风险的。我可以四平八稳的,不让读者失望,和前一部作品故事情节完全不同,但是其他方面没有多大的区别,是平面推进的作品,这种风险是很小的。但是如果要探索、要创新,就很有可能失败,是对既有的审美标准的破坏,很有可能伤很多人的心。那么,许多作家、包括有经验的读者心里其实都有一种好小说的配方,都知道以什么方式来描写或者推进,如果按照这种方式配置,还不是原创,你想打破这种方式的话,风险很大的。我的创作也出现这种现象,《红高粱》后,我完全可以沿着这个路线写第二部、第三部,写了父亲再写我,本来我也是这样想好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没有再推进的必要了。下一部就要跟以前所有的这些区别开来,没有人说我一定在马尔克斯的写作道路上走了,通过《檀香刑》的写作,我们断绝了关系,离开他很远。下一部可能跟马尔克斯在一个房间里面对面的写作,这很有可能是一场巨大的冒险。”
我问:“在不断的写作冒险中,你怎么给自己定位?”
莫言说:“我有一个基本原则,对自己的定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要来哗众取宠。我个人认为写作这个职业是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你本来就是一个老百姓,写作也是一个老百姓正常的活动,并不是居高临下、振臂一挥为老百姓争公道、争正义,要变成人民的代言人。其实还是要写你内心的话,自己的感受。如果你写内心的感受恰好和许多人的个人内心感受是合拍的,那就自然有代表性,获得普遍性。总而言之,我认为个人的定位是来不得半点虚伪的,真话假话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是表露无遗的。有人尽管说是人民作家,但是如果没有住四五星级的酒店就马上骂接待方,那不是把所谓的定位给粉碎了吗?”
谈话中提到当下涌现了一批写法新潮的少年作家,我问:“你如何看这种现象?”
莫言说:“我看过少年作家的作品,我当然知道他们的软肋在什么地方,但我也确实感觉到他们有许多我难以企及的地方,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批孩子的想象所依赖的素材不一样。我们的想象是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上,比如我要借助高粱、玉米、马牛羊等可以触摸的物质性的东西,这帮孩子已经是什么动画片、电影、电脑游戏,把别人的思想产物作为自己的思维材料,半虚拟的幻想的世界。现在也应该改变对写作这个行当的认识,过去对写作的认识就好像你一旦走上写作之路就命定要写下去,不然人家就说你江郎才尽。但是这帮孩子是带有游戏性,完全出于一种爱好,写一篇小说玩玩,写完了,证明了,不写了,可能去搞其他的了,他一开始没有强烈的事业感,没有把写作当事业,没有太大的压力。现在看有很多人担忧:这些孩子写完一部,下一部怎样呢?他们生活匮乏了,经验没有积累。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一个年轻作家的第一部是游戏之作,第二部是游戏之作,第三部就有可能不游戏了,所以写作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心态随阅历丰富,年龄增长,个人命运变化,他创作本身就会有变化。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老一点的作家跟他们的区别。我现在还暂时放不下这个担子,因为小说艺术本身还有巨大的吸引力,吸引我继续向前走,我还能写出两篇你来评判胜负的作品。大众化的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可能性,网络的出现使文学的门槛降低了,鼓励更多的人写作,通过写作来提高素养,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在深圳看到一部车后写着:写天下文章,做少年君子。对孩子来说,写作还是很好,能发表更好,不发表没所谓,就当是一种素质教育。那些年轻作家没有把文学想得那么庄严是一件好事。一旦一个人把文学想象得超越了文学本身那么伟大,那多半写不出好作品。如果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写一部伟大的作品。这是一场社会性的灾难。最可怕的是当一个作家写了一部平庸的作品,就以为自己写了一部经典作品。所以,有时候经典作品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成了经典。”
2010年1月,莫言再到广州。南方书城早已关闭,莫言的记者会设在对面的广州购书中心,我受邀参加。稠人广坐,无缘深谈,而获赠莫言签名的新著《蛙》。两年后,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