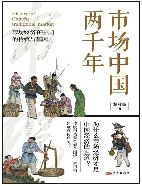19世纪广州街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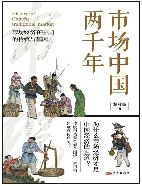
《市场中国两千年》
龙登高 著
东方出版社

《浩荡两千年:
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吴晓波 著
蓝狮子|中信出版集团

《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经济史学家龙登高的《市场中国两千年》,从早期农村公社市场的兴起和解体讲起,一直论至明清时期的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从书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在古代中国都有独特的发展,并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由此而论,古代中国市场并非“死气沉沉”,“市场经济”其实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
□明生(笔名)
司马迁的肯定
市场发展突出的表象之一,就是职业商人群体力量的壮大。他们成为令人侧目的社会力量,并引起其他社会阶层的关注。
春秋战国之交,职业商人开始活跃于中国市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许多人靠白手起家致富,呈现出务农不如务工,务工不如经商,缝制彩色绣花的衣服不如守着店面的局面。一些商人尤其是盐铁大商人,其资本之巨、财产之丰令人惊叹。
司马迁极尽华丽辞藻,铺张扬厉地加以形容,仿佛不如此不足以表现商人群体的崛起及其力量。他敏锐觉察到,这些发迹的商人,大多既不是享有特权、受爵封邑的世袭贵族,或者大权在握的当朝品官吏僚,又不是作奸犯科的罪犯,而是跟随时势的发展变化,在市场中辗转奔波的奋斗者,多数不过是原来村社中普普通通的百姓。这是时代大变动、大发展给予普通人的机遇,因为新社会需要新型的工商业来创造新的财富,活跃新的市场。
每一个成功商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创业史。卓氏被秦人从赵国掠至咸阳,又夫妻推辇远迁成都西南的临邛,在那里“即山鼓铸”,奔走于滇蜀不毛之间,才逐渐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师史在各郡国间贩运粮食,无所不至。他的家乡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经常要往返路过,却“数过邑门而不入”,无怪乎司马迁称赞说,正是凭借这等精神,师史才能积累起千万的财富。
商人的成功,离不开市场与经济环境。战国时,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商人的作用,因为商人到来必然会创造消费需求,从而带来收益。《管子·侈靡》说,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庸碌无为的人。他们不挑剔居住的地方,不挑剔所侍奉的国君。卖出货物是为了牟利,买进货物也不是为了收藏。国家的山林,他们拿来就能以此赢利。市场所到之处,就会倍增国家的税收。管子已经认识到,商人可以创造财富,带来繁荣。商人不分地区、不分国君,唯利是图,因此统治者应该为商人提供较好的市场环境,吸引商人前往。另外,管子已经意识到“无市则民乏”,没有商人的运输贩运,市场商品就会匮乏,人民生活无着。
《市场中国两千年》注意到,力主重本抑末的韩非子,也主张加强市场联系。《韩非子》就告诫君主们,要让商市、关口、桥梁畅通,从而使人们可以用自己有的东西来换取没有的东西。当客商纷纷来到本地时,外来的货物就留了下来,财政收入就会增加。韩非子主张严格税制管理,杜绝重税与刁难商人,与今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思路不谋而合。
从整体看,虽然战国秦汉时期交通运输条件还很有限,城乡市场还没有形成有机的网络,但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经济中心。以洛阳、临淄、成都、长安等大城市为枢纽,依托日渐进步的交通运输网络,沟通各地市场联系与商品往来,全国大市场已经有了雏形。
统一大市场
自汉末军阀混战至隋朝统一的400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割据纷争的时代,又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大土地所有制下的地权转移与庄园经济,在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地权转移对田地市场,庄园经济对市场商品供给,士族门阀地主对商品流通,都产生了独特而深刻的影响。
此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由赵宋王朝一举削平,与之并存的,西南有吐蕃、大理,西部有西夏,北部先有辽国,继起的金国更与南宋长期对峙,直到元朝才实现了全国的真正政权统一。历代史籍皆称宋代“积贫积弱”,但这只是政治军事的反映。从经济方面看,中晚唐以来的市场变革继续深入和发展,11—13世纪,两宋时期达到了传统经济的新高峰。
然而,宋王朝毕竟只有半壁江山,到了明清,全国大市场才得以进入成熟期。《市场中国两千年》认为,明中叶后,市场与社会继续发展,民间经济能量得以扩大,微观主体的功能得到强化,甚至形成了基层与政府之间的市场化连接纽带。与常规认知不同的是,当时中央集权与专制政府管控严厉,其实主要针对官僚体系与地方政府,属于政治上的强力管控。而对于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政府更多实行的是“自由主义”,希望以自主、自立、自治的模式实现民间治理,这就促成了明清市场主体进一步发育。
先看规模。以商税间接观察市场规模与兴衰,是经济史研究中的常规方法。明中后期,钞关税收定额由隆庆年间的29.4万两,上涨为万历年间的33.57万两、天启年间的44.22万两,至崇祯年间涨至78万余两。清代各关实征关税总额也由顺治九年(1652年)的100万两,增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470万两。虽然有学者指出,以明清面向商业活动征收的流通税来还原市场流通总额难以实现,但从流通税的增长趋势来看,明清时期跨区域贸易的总体水平和市场规模的积极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再看流通。劳动力的流通,表现为大规模国内移民和城镇化。前者是明清时期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之一;后者多见于东部发达地区,如江南市镇普遍吸纳外来劳工进入纺织行业。资金的流通,可从信用工具的创新中窥见一斑。18世纪以来,账局、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出现,晋商于19世纪通过在金融领域的成就独领风骚,建立了其全国性的金融网络。信息领域的流通,同样值得关注。一方面,政府实行奏报制度,特别是清代晴雨粮价奏折,使得价格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更公开;另一方面,商人群体从事各种商业情报收集工作,并通过同乡、宗族等在各地传播。
《市场中国两千年》据此认为,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商品、劳动力、资金和信息的流通都显示,到了明清时期,一个全国市场已经在中国形成。而全国范围内的市场整合,也进一步加强了区域专业化分工和商品、劳动力、技术、信息的流动。因此,各区域市场日益活跃。其中,江南作为东部地区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其市场发展水平令人瞩目。此外,伴随白银货币化与海外白银流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凭借稳定充足的货币供给,中国得以融入国际市场。
“藏富于民”
“中华传统文化与制度排斥市场经济”,持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为韦伯,其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论调,已为实践所证伪。但今天仍有不少人主张,古代中国不存在市场发展的制度与秩序,或者说传统制度下商业与市场秩序得不到保障。《市场中国两千年》则认为,古代中国强权掠夺商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制度化,并非常态化,更不是主流存在。
可以发现,传统商业与市场具有活力,民间经济时有创新,世界最早的纸币就是民间创新的商业成果,晋商、徽商的经营创新呈现现代性等,都是古代中国市场经济的闪光点。
其实道理很简单。朝廷获取土地产出和社会剩余,最稳定和可持续的途径是什么?是直接占有土地还是向农民征税?是政府直接经营商业还是向商人征税?答案当然都是后者。对商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土地财产,要向政府交税。流动性商业征税在技术上不那么容易实现,所以直到宋朝,政府才系统性开征商税,使政府稳定获得商业剩余。此后,商业税成为与土地税并列的主要税收来源,这两块都有商人的贡献,所以在逻辑上,各王朝不会或不必抑商。
正因如此,即使是大规模打击和掠夺商人的汉武帝,在执政后期时,重农抑商政策的力度与频度已经有所减弱。汉武帝南征北战,打空了文景之治留下的丰盈国库,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固然嫉恨商人有钱,实行“算缗”“告缗”,但也希望千方百计增加政府收入。因此,他选拔“兴利之臣”,如“言利事,析秋毫”的桑弘羊等,允许官员列肆贩卖,希望通过国营商业来增加政府收入。
此后历史中,政府对商人的额外征敛普遍比较慎重,有时间与范围的限定性。比如捐输报效,在时间上一般是在战争或者发生灾害时才会要求商人捐钱捐物,相当于共赴国难。在对象上主要来自盐商、十三行等专卖或垄断行业。盐商、行商所获超额利润,常常通过“报效”“捐输”的形式转入官府。但他们又通过政策得到了物资补偿,如加耗报效,盐商于例定引斤外,加耗盐若干斤,作为“报效”的回报。再比如抄家。据学者统计,清朝被抄家的商人几乎都是与内务府有关的商人,即通常所谓“皇商”。这些商人由内务府领出巨额“帑银”,行盐或办铜、采买木植,一旦资本不能归还,即被查抄家产。本质上看,这些人并非合法经营的商人,而是扰乱经济秩序、侵害国家利益的蛀虫。
《市场中国两千年》进一步分析指出,古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以“藏富于民”为正统,以“与民争利”为羞耻。即便有行政专卖制度,但也限于少数特殊商品,比如盐、香料、酒、茶等,从整体看,政府直接经营的商品或领域是非常有限的。司马迁推崇的治国之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种朴素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其实是后续两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如今,国家提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当我们以市场经济的历史视野去审视时,可以更好地把握历史渊源流变与长期趋势,理解其中的深意。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