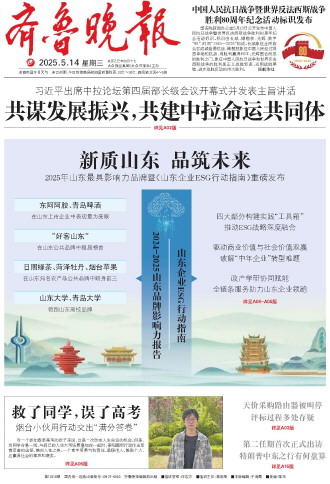□李怀宇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终其一生,陈先生并未在宋史上有专著。海外别开天地的宋史学者,则是刘子健。
刘子健的《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是他在1963年于香港出版的《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一书的英文缩写版,稍作修改。欧阳修(1007-1072),天资卓颖、精力旺盛且多才多艺。今人熟知欧阳修,视作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尤其是文学家。刘子健则认为,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学家之列,欧阳修还要通过“历史长河的竞争”这项测试。杰出的士大夫应当是“全才”,其个人不仅是传统的化身,同时还要为传统增光添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只有寥寥不足百人享受陪祀孔庙的殊荣,欧阳修便是其一。
学者普遍认为宋代是新的社会形态与文化模式的形成时期。一些史学家称之为某种“文艺复兴”;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宋代是“早期现代”的发端。刘子健认为这种种论断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试图将中国历史装进欧洲历史的参考框架内。其实,两者之间最多具有相似性,不能用欧洲历史的框架去解释中国历史。刘子健提出了“新传统”发展阶段的概念,这一阶段始于晚唐,定型于宋初,前后持续了近一千年。所谓新传统,本质上是指将特定古代文化传承与变化因素相互整合形成。这一新传统并未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贯穿了整个中国社会,并触及广大民众,比旧传统更难改变。由于这种新传统是通过新旧两种因素交织而成,总是阻碍彻底的改变,更遑论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了。最终,新传统的保守取向导致了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欧阳修年轻时,家贫无藏书。在登门拜访一位富有的李姓朋友时,欧阳修在一个破旧的筐中发现了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韩愈是唐代伟大作家,又是新儒家的先驱。欧阳修被韩愈的古文深深折服,并暗下决心,自己也要掌握这种文体。欧阳修乐于交友,从中发现“天下奇士”。在任翰林学士时,欧阳修随身携带数十张空白拜帖,每当听到某个陌生人备受赞誉,他就会打听此人的住址,递交拜帖,然后前去拜访。若确定某人极具潜力,即使是辗转通过友人得知的消息,只要觉得友人的判断可靠,欧阳修就会把这位新人举荐给能够提供帮助之人。欧阳修用这种方式帮助了整整一代年轻才子。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儒学宗旨,即君子是国家与社会的基本财富。从心理上来说,欧阳修乐于助人的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他在孤独的青年时代进行过的种种奋斗。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和韩琦奉诏进入天章阁,与欧阳修志同道合,推出了奏疏《答手诏条陈十事》,为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与二十多年后的熙宁变法相比,庆历新政只是一个温和的施政纲领,旨在现有框架内实现改良,不主张对法律或政策作重大变革。欧阳修作为改革的关键人物,事先告诫皇帝,必有很多官僚反对改革。招致最多反对的改革建议,当然是减少恩荫官员的人数。果然,庆历新政很快遭遇反对。
庆历四年,宋仁宗就所谓的朋党问题向范仲淹发难,范仲淹大胆重申了自己长期以来秉持的信念,并反问道:“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随后,欧阳修进呈了《朋党论》。这篇奏疏被认为对儒家思想做出了原创性的杰出贡献。实际上,君子有党的思想并非出自欧阳修,而是出自范仲淹。但欧阳修加入了惊世骇俗的一点,即小人甚至连结党的能力都不具备。欧阳修在撰写《新五代史》中,指出可以轻易地将“朋党”一词进行拓展,用以涵盖任何社交群体,比如亲戚故旧、交游执友、宦学同道、门生故吏等等,而从历史上看,小人经常以“朋党”这一罪名来诬陷无辜之人。欧阳修怀着挽救范仲淹与改革的希望,像律师一样据理力争,将委托人的供认转变为一场令人赞叹的辩护。在整个王安石变法时期、随后的反变法时期及后变法时期,欧阳修为朋党所作的辩护一直激励着下一代人。
庆历新政后,欧阳修因遭人诽谤而被贬谪,辗转多地任职长达十年。欧阳修为诗为文,研究学问,对其历史地位倒是大有裨益。欧阳修在滁州保持良好的心态,自称“醉翁”,这个名号也因《醉翁亭记》一文而流芳百世。实际上,当时欧阳修刚过不惑之年。庆历八年,即被贬三年之后,欧阳修升任扬州知州,扬州是大运河与长江交界处的大都市。由于担心政敌心生嫉妒并试图再次痛下杀手,在任未满一年,欧阳修就请求改任到较小的地方。他调任颍州知州,这里湖泊众多、风景优美,后来成了欧阳修永居之地。
在欧阳修晚年,王安石打开了拜相大门。王安石的宏大改革计划很快在熙宁二年(1069)拉开了序幕。在欧阳修看来,熙宁新法过于笼统、不合常规且令人烦恼。他既不赞同新法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也不赞同其高度自信的管理模式,因此,他明确表示,绝不参与其中。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倡导者之一,也是熙宁新法的反对者之一。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欧阳修认为汉朝学者是糟糕的史学家,因为他们将“奇书异说”融入其历史著述中,这些“奇书异说”有时是根据传闻得来,有时甚至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想象得来。司马迁的《史记》也受到欧阳修的批评:“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惟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也。”欧阳修认为,收集史料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步,务必做到详尽无遗。史料一经发现应当尽快记录下来。
欧阳修在历史领域的成就主要是撰写《新五代史》和参与编修《新唐书》。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有贬有褒。欧阳修发明的另一项技术,可以描述为“通过交替使用抑扬来进行补偿”。在为大体高尚之人作传时,欧阳修会强调他的主要成就,不提及他的轻微缺点;但在史书的其他部分谈及相关主题时,则会全部指出此人的这些缺点。
在现代人看来,欧阳修最伟大的成就是文学。苏轼认为欧阳修的古诗“似太白”。王安石则认为欧阳修的诗歌水平“居太白之上”。苏轼、王安石都曾受过欧阳修的提携,他们的评价可能有夸张之嫌。但欧阳修之诗确属一流水准。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影响深远。
欧阳修声称在文章风格上师从韩愈,后来这一风格被称为古文体。韩愈世称“昌黎先生”,欧阳修等人便从中撷取两字,自称为“昌黎派”。在中唐元和时期,韩愈致力于重振儒家,他主张将儒家理念运用于文学中,称“文以载道”,要注重文章的说教作用。历史上的评论家认为,欧阳修将古文推向极致的艺术高度。他使用最普通的词汇,文章却优雅且令人称奇。如在《醉翁亭记》中,“也”被用在每句的句末,共出现了21次,这表达了一种愉悦的心情,也创造了一种韵律的停顿。唐宋八大家,欧阳修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完善了两位前辈开启的文体,还鼓励着同朝代其他五位大师。曾巩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阳修在至和二年(1055)和嘉祐元年(1056)两度举荐王安石,那时两人甚至还未曾见面。欧阳修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歧从未抹杀两人之间的友谊。欧阳修去世时,王安石在祭文中说:“天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欷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走,又予心之所仰慕而瞻依。”欧阳修对三苏皆有提携,尤其欣赏苏轼。欧阳修对苏轼说:“吾老将休,付子斯文。”
重寻欧阳修的人生历程,刘子健认为:“欧阳修的性格更适于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而不是一个身居高位的官员。他最大的成就在文学,这证明他具有更偏向艺术的才华,而不是倾向实用的政治能力。欧阳修的卓越在私人生活与工作中均有体现,只不过通过一种令人震惊的相反的方式。欧阳修不涉及政治的文章留下许多名篇。在生活中,他很适合相伴,与他交谈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一旦涉及政务,欧阳修似乎言辞过于犀利而非能言善辩,他尖锐有力、毫不妥协,并不是一位容易共事的同僚。欧阳修更愿意赢得所有争辩,而不愿妥协……欧阳修是经过多年在政治、文学与学术上积累了较高声望才得以在政坛持久为官。”
从儒家的历史中定位,刘子健评价,欧阳修拥有酷爱钻研的头脑和不安的灵魂,在新的方向与领域不断探索,这正是新儒家早期精神的体现:“从黎明到耀眼的正午,再从正午到金色黄昏,欧阳修始终在宋代的思想天空闪耀着,虽偶尔被云翳遮蔽,但一直是最耀眼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