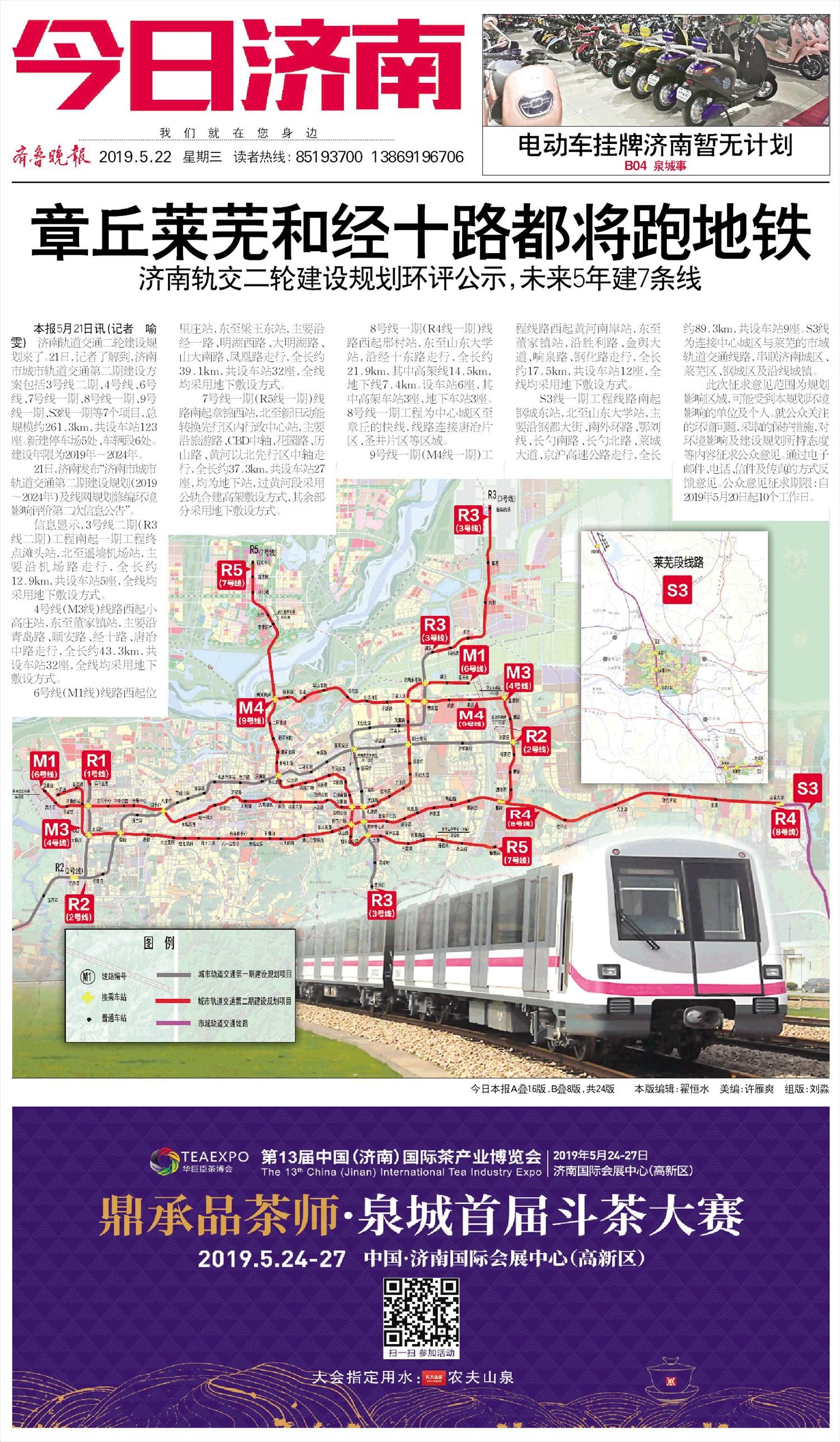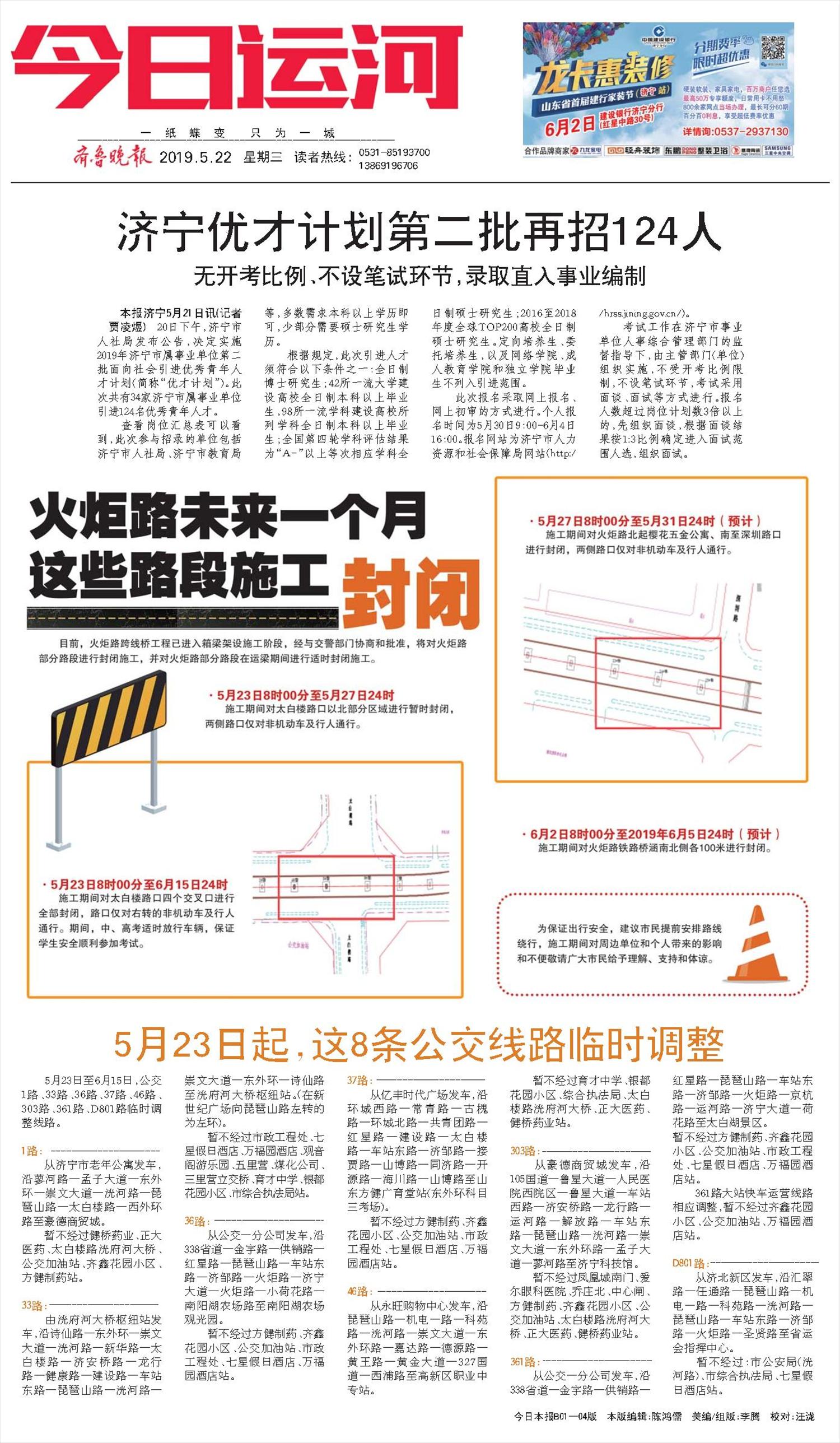对我来说,有些电影,是很难给出客观评价的,例如《过昭关》。《过昭关》的故事并不复杂。亦舒说,没有三句话概括不了的故事。《过昭关》甚至不需要三句:七十岁的爷爷李福长带着七岁的孙子宁宁,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去千里之外看老友的故事。
爷爷生活在乡下,生命已经向着凋零而去,他住着简陋的屋子,吃简单的食物,生活极度简单。偶然听到老朋友生病的消息,立刻决定骑车出门。因为,他和这位老友之间,有友情,更有恩情。他当年在运动中落难,这位老友曾经救他于水火。但故事的重点,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路程。爷爷带着孙子,在夏天的远足,才是故事最动人的部分。这一路上,他们经过村镇,经过河流,经过树林,经过山谷,他们在路边撒尿,在玉米地里睡觉,星星在他们头上。他们也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河边钓鱼的年轻人、山谷里养蜂的哑巴、开大货车的司机,和他们有过交会。
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里,还有几个小故事,都是由爷爷讲出来的。讲故事,是为了排遣寂寞,是为了让孙子知道一些人世间的道理,也是为了和路途中遇到的陌生人交流,有的时候是劝慰,有的时候是纾解。爷爷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这个故事,却是以戏中戏的形式呈现的,京剧人物装扮的伍子胥,穿过山林,经过飘着薄雾的河流。第二个故事,一个发生在乡村的生死故事,也是由另外的演员演出来的。两个故事,都配着爷爷苍老的声音,他像个说书人,说古代故事,也说自己经历的世事。
但最动人的,不是这些景色、这些故事,而是那些很细的细节:爷爷给宁宁洗脸洗澡,爷爷带着宁宁在路边撒尿,爷爷在三轮车上铺下被褥安顿宁宁睡觉,还有在河边,看到有人在钓鱼,爷爷用树枝和饮料瓶子也做出了一套钓鱼器具。爷爷笃定、安然,无所不能,就像那篇安徒生童话的题目《老头子做事总是不会错》。
有人说,这部电影让人想起大卫·林奇的《史垂特先生的故事》以及北野武的《菊次郎的夏天》,也有人想起侯孝贤电影中的若干情绪和细节。事实上,如果单论电影的动机、用行走架构整个故事的方式,这样的电影,在日本电影里就有许多。但对我来说,《过昭关》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人生的框架不外如此,人生的故事大致相仿,但那些细节、那些体验,却只属于经历过它的每一个人。《过昭关》让我想起的,是爷爷和我在农场的往事。
五岁以前,我是由姥姥姥爷(我们这边一律都叫爷爷奶奶)带大的。我们生活在新疆南部的于田农场,爷爷、奶奶、舅舅、小姨,我们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农场种植了小麦、棉花、苜蓿、百合和各种蔬菜。农场之外,是几万亩胡杨林。
很多时候,爷爷带着我在田间地头辨认植物,给我讲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种植方法。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他带着我在菜地里除草,然后把铲下来的野草埋进一个大坑里,用来沤绿肥。那种不受人待见的小蓟草,带刺,一长就是一大丛。爷爷却说,这种草用来沤肥是最好的。那以后多年,我在野外看到多汁的野草,心里总是跃跃欲试地想把它砍下来沤肥。
我的爷爷奶奶,也和《过昭关》里的爷爷一样,给我灌输很多人生道理。他们都是经历过饥荒的,所以很痛恨浪费粮食。如果我吃饭的时候剩下一点,奶奶就会用非常严厉的语气说,浪费粮食是要被天雷打的。所以,直到现在,聚餐的时候,我都会努力地把分给我的食物吃完。剩菜剩饭太多,我都惴惴不安很久。
所谓亲缘,就是在这种静静的日子里一点一滴地累积出来的吧。看《过昭关》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起的就是农场往事。李福长像所有的中国老人一样,面容平静,恬淡隐忍,过着简单的生活,但他的心里是有风暴、有大海的。只有和孙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表现出一点想把这种风暴、大海一样的阅历传递下去的欲望。这种欲望,只有亲人之间才会有。过昭关、过潼关、过山海关,关关难过,煎熬都要自己承受,传给亲人的,却只有千锤百炼后的一点人生智慧。拥有这样一位长辈,是幸福人生的开始。
我懂得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或者再晚一点的80后,大概也都懂。所以我们是很难客观评价这部片子的,我们的评价里,必定会带着山呼海啸的往事,带着童年夏天的一次次远足,带着家人逐渐消失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