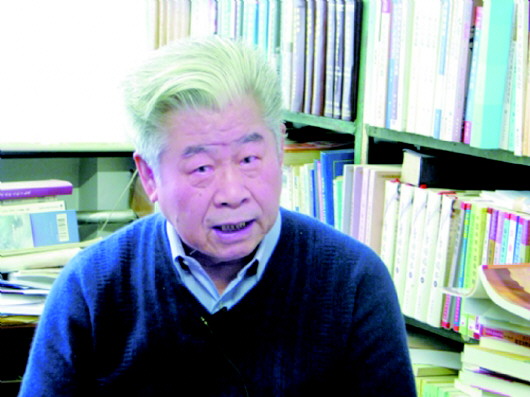史学家回望历史警示改革:
甲午前的改革没能凝聚共识
2014年09月1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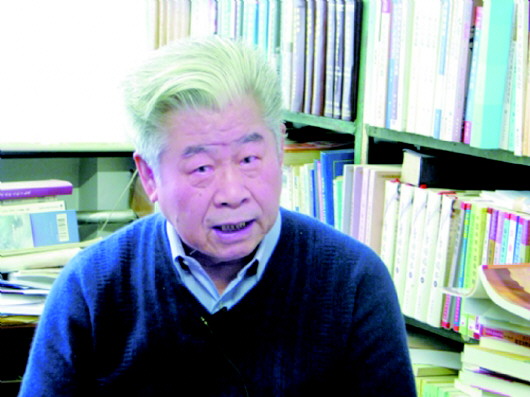
张海鹏

戚俊杰

马勇
诚如教科书说的一样,这场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洋务运动改革的不彻底。有人说,假如清政府及早彻底改革,也许就不会爆发甲午战争,即使爆发也不至于惨败。但历史没有假设。是什么原因导致改革不能彻底进行?是国民意识不够,还是中央没能全面牵头?一部甲午战争史,无不是一部艰难改革的历史。
为此,我们专访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原馆长戚俊杰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他们提供给我们今天看待这场战争的一个不同的视角。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洋务运动只学技术根本不行
齐鲁晚报:甲午战争是不是我们败在准备不足?
张海鹏:日本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和准备,包括经济上、军事上、社会动员方面的准备,以及国际舆论准备,而且它涉及多种进攻中国的实施方案。
这一些在中国都没有。在我们的文献上看不出来当时清政府在应对日本方面做过什么准备。日本方面在中国收集情报的人,很多都是名人,比如日本有个人(为桂太郎——编者注)回国以后写了《邻邦兵备略》,这个邻邦就是指中国,介绍了中国军备的准备情况。还有一个武官写了《征清意见书》(为驻华武官福岛安正)。英国海军后来发现,还有六份征清方策,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也许还没被发现。
此外,日本有一个举国战争的体制,包括政治、后勤、外交方面,都做了周到的安排,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国内已经形成了集中讨伐中国的民间情绪。
戚俊杰:(准备不足)肯定是一个原因。我们有些人是到了一个关键点,比如甲午战争100周年、120周年才进行反思,这是不对的。平时就应该进行反思,有警醒意识。我研究甲午战争这么多年,得出一个经验教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哪怕一个人,做事都需要主动,被动去发展、思考,这样永远不行。我们不侵略别的国家,但不代表我们不主动防御。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甲午用了26年,政治、军队和外交都做了充分准备,既有框架,也有具体措施。战前,日本思想统一,士气高涨。
林则徐虽然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强调建设海军,但意见没有被采纳。魏源的《海国图志》,至今我们还能看到这本书的先进性与引领作用,但在中国不被重视,反倒在日本非常受欢迎,被视为理论教材,海权、海洋意识在日本人心中扎下了根。
齐鲁晚报:有人说洋务运动的不彻底性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戚俊杰:有关联性。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的皮毛,“中体西用”,只学技术,这根本不行。
那时候,一则意识不到全面改革的必要性;二则,当时既得利益集团太庞大,地方大员根本无法消除障碍。改革一旦到了深水区,或者进行不下去时,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集团。清末,虽然经费紧张,但用于改革图强、海军建设方面还是可以的,只是因反对声太大,大量经费被腐败,所以要坚决反腐,这样才能去除改革的障碍与壁垒。
相比之下,日本明治维新,举国上下形成共识,思想统一,行为上,天皇等还带头节俭。
张海鹏:洋务运动严格说来,它不是一个全国性的,不是一个在中央统一指挥下发动的一个所谓现代化的运动,只是地方大员在某些省份发起的,而在朝廷、在中央,实际上慈禧太后并没有积极支持洋务运动,而且朝廷的很多人反对洋务运动。所以洋务运动在中国开展30多年,规模仍然较小。
巨额赔款让清政府无力再做大的改革
齐鲁晚报:对于改革,全国上下,特别是普通民众是不是必须得有共识,或者一些现代的意识必须扎根?
戚俊杰:是的。日本在建设海军方面,天皇和伊藤博文都捐款,下面的普通老百姓意识到海军的重要性,也捐款,因为他们对建设海军的必要性有了认识。
齐鲁晚报:甲午前,中国的普通民众没有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这是否该归责于我们刚刚被迫打开国门?
戚俊杰:不能简单地这么讲。日本也是被迫打开国门,但日本人思想意识转变非常快,主要是他们危机意识特别强。中国向来以天朝自居,对西方的事物动不动嗤之以“蛮夷”等等,思想中还多少有些自大。
有时还要看国家最高统治者的能力和意识。如果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没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不去对国民进行宣传和教育,老百姓就更不知道了。但日本却不断对国民强化教育,这就是差距。
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有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全面深化改革,都是就改革等先在思想上达成共识。联系到当下的反腐,从上到下形成了思想上的统一,既打大老虎又打苍蝇,这非常值得肯定。
张海鹏:梁启超讲“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在甲午之后,我们就有不少国民和官员意识到海军建设、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还有很多现代性思维也开始慢慢产生。只是在这次战败后,清政府付出了很大代价,光赔款就达2亿两,已无力进行大的改革。变法失败后,革命等各种救亡图存的呼声和行动很多,各派之间无法达成统一的共识和行动,中央政府的命令也很难得到贯彻。
马勇:明治维新思想家一直在启蒙日本民众,日本必须走出海岛、踏上大陆,与世界诸强竞争。但中国没有,这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刘亚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我非常赞成这种观点。
齐鲁晚报:在甲午战争中,个人英勇是否与整个体制形成鲜明对比?
戚俊杰:正如你在博物馆看到的史料,很多小人物还有大人物都表现得正气凛然,要么战死,要么自杀成仁。上世纪90年代,我们组织甲午海战研究,有很多大学生前来学习。那是8月份,大学生随船去参观过去的战争地点,结果有人抱怨,呆在船上太难受,而那个季节的海风吹着其实还算舒服。你想想丁汝昌,60岁的人,身负罪名,在寒冬中带着北洋水师进行战斗,直至最后自尽。
个人显然无法扭转体制的弊病。当时的水兵陈京莹在家书中写道,“以儿愚见,陆战中国可操八成必胜之权,盖中国兵多,且陆路能通,可陆续接济;但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贪腐、海军建设不受重视、各水师只顾自己利益等等,使得北洋水师几无胜算,陈京莹认识到了这点,但还是战斗到死。
甲午战败促成民族国家意识产生
齐鲁晚报:甲午战争影响真的那么深远?
张海鹏:一个世纪了,我们还可以感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甲午战争把我们的宝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在洋务运动时期,台湾是中国各省当中办得比较好的,当时叫模范省,而这个模范省在1895年被日本正式割去,台湾人民至今还为此心痛。
马勇: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本来洋务运动等还是比较自信地进行着,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自此使得中国人开始自我怀疑,变法、革命等等都出来了,思想有七八种。与此同时,清政府在割地、赔款后,也意识到日本值得我们学习。既然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为何日本能进行改革、能变得强大,我们就做不到?此后,大规模的留学生去往日本,从学欧美转为学日本,鲁迅、黄兴、宋教仁、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等人都去日本学习过。
甲午战争后,中国思想界非常活跃,但最后要归结到朝廷才有用。在中国,知识人再厉害,最高领导人不拍板也没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也进行沉痛反省,认识到之前做得还不够,比如对社会的释放还不够。在甲午战争后,清廷还真放开了,允许自由办报,一下子几千份报纸就出来了;还可以自由议政,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政治改革,什么都能谈,这就释放了一个言论的空间;另外,还允许自由结社,全国马上就有几千家新兴社团出来了,有专门研究现代化学、现代农业的,也有关心国是、只谈政治的。
正是甲午战败的打击和反思,引导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如果没有这场甲午战争,我们可能还无法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我们去看梁启超的作品、康有为的作品,他们所强调的大概都是这个意思,这是中国民族几千年来的一次大觉醒,之前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一个文明体,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古代中国的“天下”、“国家”意识和我们后来讲的近代国家完全不一样。
齐鲁晚报: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你参与了全部建设,是什么支撑你这么做?
戚俊杰:我在刘公岛上工作了20年,接待了很多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将领。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影响太大,我们必须深刻反思,还要将甲午战争中的点点滴滴介绍给人们。1992年前,那时并不叫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一开始叫北洋海军提督署文物管理所。后来我就主动找人,想在甲午战争100周年的时候,能让中央领导题字,这样既方便工作,也让人意识到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最终在1994年,江泽民同志题词。我还和博物馆走访了不少北洋水师将领后代,不少人被我们打动,将手中的文物捐给博物馆。
如今,大家看了这些文物和历史资料,肯定脑子里会留下印象,有的还进行反思,自发建立海权、海洋意识。再比如,意识到我们中国必须发展好自己,实力强了才能不被人欺负。实实在在说,中华民族当前在海洋上,特别是在东海和南海所面临的困难处境,远远超过甲午战争的时候,确实需要中华民族齐心协力、全力以赴。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