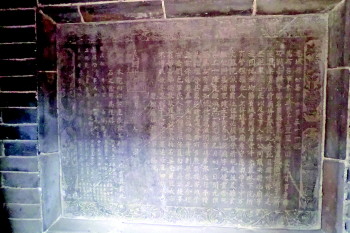讲书院记忆
2014年03月1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讲书院后殿。

讲书院大雄宝殿前的古树。

“讲书院”已成重点保护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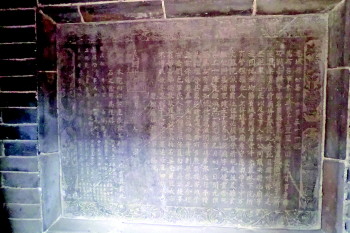
讲书院民国时期的碑文。
讲书院建于元代,原名福盛寺,归济南府净居寺管辖。据碑文记载,明万历年间,该寺达到鼎盛时期,有僧众近百人,成为高僧们讲诵经卷的中心,遂易名讲书院。
□周和平
小时候,村子南面有一座古寺,叫做讲书院。耸立的石碑、蔽天的古木、飞檐斗拱的大雄宝殿以及从庙前蜿蜒北去的巨野河,常常塞满我童年的梦乡。夏日里,山门下凉风习习,伴随着潺潺水声,从那帮拾粪老人的胡子里争相奔流出一串串或庄或谐、或素或荤、或人或鬼的故事。
日升月落,冬去春来,讲书院里里外外演绎过多少人间悲喜剧,谁也说不清楚。有些故事从老人们的胡子里过滤出来,便形成多个版本,版本之间有的相近,有的则相去甚远。老人们都说个人的说法是嫡传正宗,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有人打趣说,要不叫起和尚来问问!于是,争端得解。因为,1948年济南解放后,庙里的和尚早已风去云散,不知所终;若问,只有问寺西那座座青冢,那里是历代僧人的墓地。坟头蒿草索索有声,是逝去和尚的亡灵在评判吗?恐怕谁也不知道说的什么。
时下的情景才是真的。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孙村区公所在寺后的庙田里建起一溜溜猪圈,这里成了生产自救基地。穿过曲径回廊,随风传来猪们交配时的欢快叫声。
夕阳西下,人们作鸟兽散,化作村道上一个个移动的符号。几个例外者隐入寺东庄稼地。几天以后,从附近村子传来消息,刘老汉将猪场扔到枯井的瘟猪弄回家饱餐一顿,也染上瘟病,一命呜呼了!
漫长的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人们的苦日子却没有过去。猪场垮台后,讲书院先后改为油坊、粉坊、磨房,都是我们小孩子闻所未闻的玩艺儿。少年不知愁滋味,小伙伴们提筐挎篮,漫游在讲书院内外,拔野菜、捡煤核、拾柴禾。劳动之余,便把着门缝看大殿里的佛祖塑像、玄道神,偏殿里的牛头、马面、吊死鬼儿。
日子细水长流般过去,不经意间,一场更加漫长的人祸降临讲书院。一队队戴着红袖标的男女闯进山门,先是将一个个殿门撬开,把大小神像悉数砸烂,继而爬上飞檐,将上面的装饰物全部捣毁。功德圆满后,在山门前振臂高呼: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以后的日子,讲书院失去了过去的辉煌。昔日在山门下吹胡子瞪眼不服输的老人群体土崩瓦解,其中还有几位宁可在烈日下拾不着粪白跑路,也决不敢加入神侃的行列。听说他们“成分”不好,大概是地富反坏右吧。
庙田归了寺北的杨家村,柏树林归了寺南的新庄村,大雄宝殿作了公社兽医站,殿前的两棵古槐,据说与讲书院(福盛寺)同岁,不知被哪个村用炸药轰倒,做了烧石灰的引柴……只有几间破厂房、几十个工人构成吹制灯罩的车间。
巨野河呜咽北流,哀叹高僧选定的风水宝地经不住时代的风雨。
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晃几十年过去,改革开放使讲书院从噩梦中醒来。昔日的灯罩车间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成为今天拥有千余名职工、上亿元固定资产,产品远销世界几大洲的济南晨美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加入WTO,为晨美带来难得的机遇,讲书院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大概这里的风水真好吧,晨美还出了一位聋人作家——李圣元,在齐鲁乃至华夏遐迩闻名。当年那位为讲书院选址的老和尚如果泉下有知,定会为自己独具慧眼而笑成弥勒佛。
讲书院,山门还在,大雄宝殿还在,钟楼还在,更弥足珍贵的是院里那两棵与寺同龄的古柏还在,它们都在晨美公司院内,如今已是济南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为济南高新区孙村中学高级教师,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